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的时代。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朱伟
八十年代,朱伟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就职于《人民文学》。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到另一个作家的家里。在此期间,朱伟相继结识了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并推出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位置上退休之后,朱伟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系统重读和点评了10位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经典,《重读八十年代》诞生了。
莫言的1985,像一道光耀亮文坛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文学领域同样迎来了繁荣和开放,涌现了莫言、余华、苏童、马原等一大批作家和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重返文学的“黄金时代”,重读那些激情与浪漫,我们以文学为镜观照社会变迁。本期我们将重读莫言,1985年,莫言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受到文坛瞩目,他用自己瑰丽奇谲的想象为新时期文学添加了精彩的一笔,也扩展了新时期小说的创作空间。本期前《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将带领读者们重温莫言的《红高梁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经典作品。

人物简介: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因《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文坛极大轰动。2011年凭借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因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
莫言是笔名,真名管谟业。谟是谋略,也是谋国事的一种文体。莫言21岁离开高密,到烟台黄县当兵;24岁调到保定,任政治文化教员;保定成了他创作的摇篮,他最早的小说都发表在保定市的《莲池》上。1983年在《莲池》上发表的第四篇小说《民间音乐》,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篇小说帮助莫言离开了保定。它先得到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老先生的赞赏,时解放军艺术学院组建文学系,正招收第一届学员,莫言就带着这篇小说与孙犁的评论,到北京报名。

《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1985年第二期《中国作家》上,发表后专门开了座谈会,真有一下子耀亮整个文坛的感觉。我后来才知道,创作冲动其实源于莫言儿时随石匠打石头、铁匠打铁、偷萝卜、小小年纪就被侮辱的悲凉烙印。它当时在文坛形成的轰动效应,是因太强烈的表意能力:那个长长脖子上挑着一个大脑袋,从头到尾都不说一句话,全身都像煤块一样泛出黑亮光泽的黑娃;以及被铁匠房的炉火映成青蓝色的铁砧上,被火光舔熟的那个晶莹透明,泛出金色光芒的萝卜,感觉太强烈了。那萝卜飞出去,就划出一道漂亮的金色的弧线。在那个前卫作家刚开始意识到意象对于艺术之作用的年代里,它真构成了一种炫目的,甚至令人震惊的效果——在1985年,还没人能将意象表达出这样一种凹凸感夸张的油画般的感觉。
随后创作的《球状闪电》《爆炸》,继续表达情感无奈与乡村的压力。小说开头,莫言写“父亲的手缓慢地抬起来,在肩膀上方停留了三秒钟,然后用力一挥,响亮地打在我的左腮上。父亲的手上满是棱角,沾满成熟小麦的焦香和麦秸的苦涩。六十年劳动赋予父亲的手以沉重的力量与崇高的尊严,它落到我脸上,发出重浊的声音,犹如气球爆炸”。慢动作般写这记耳光,我记得洋洋洒洒写了三页稿纸。这是家庭压力的象征。
莫言在1985年的姿态,是要逆那些一环环讲线性故事的方法。他说:“没有故事就是最好的故事。”他以大量触觉鲜明的感觉支持绵密的叙述,他写麦秸在阳光下爆响,到处都反射着光线,使“所有颜色失去颜色”;写“尖锐的麦芒上生着刺毛,阳光给它们动力,它们互相摩擦,沙拉拉响”;将蝉噪喻为“爆竹的裂片,碎片像雪片在空中浮游”。色泽、音响、味觉如霰扑面而来,真是想象力恣肆。莫言的强大,就在他这种非凡的叙述繁衍力,我称它为“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在1985年,他的才华就像冲决了闸门那样激扬迸射,飞珠溅玉,似乎只需一个意象繁衍,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就如舒展地吐出一口长气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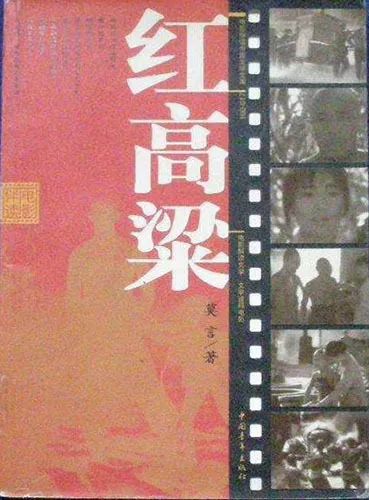
那时约稿叫“订货”。一个优秀作家“井喷”后,就像一块储量丰富的油气田,我就会紧盯他的下一部。《红高粱》由此发表在1986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上。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叙述“我父亲”、“我奶奶”与“余司令”,这样可以突出主观感受,更重要是以主观感受超越情节。情节从14岁的“我父亲”跟着余司令的队伍去伏击日本汽车队始,但结尾才用三节篇幅浓墨重彩写伏击。第一节先用整整一节写高粱地这个传奇发生地的意象,他形容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海洋”,然后写高粱地里的雾气,写天地间弥漫着高粱的红色粉末。洸是水光,洸洋是水无涯际,正是莫言对高粱地这样动人的描写感动了张艺谋,也使他以后的电影里,再离不开这种繁茂的鲜绿了。
结构上,莫言是先从罗汉大爷写起,写“我奶奶”与他暧昧的悬念,写罗汉大爷本可轻松逃脱劳役,却因他家的骡子而被打成血肉模糊,然后大义凛然地被凌迟。中段才写“我奶奶”被颠轿,余占鳌制伏了劫路者,却有意不写余占鳌如何成了“我爷爷”,反而插出来一个说“大英雄自风流”,昂首阔步走过余占鳌从背后射来枪弹的任副官。最后,才集中写那段“我奶奶”回娘家路上,与余占鳌荡气回肠的野合,写酣畅淋漓的悲壮结尾。这个叙述结构很显示莫言的大气:罗汉的凛然,“我奶奶”在被劫时大大方方跨过轿杆,站在矢车菊里烂漫的笑,甚至任副官头也不回同样凛然地走,都是为最后三节做铺垫。他要在“我奶奶”死前,才写她与余占鳌野合时,“炽目的阳光在高粱缝隙里交叉扫射”的感觉,这阳光与鲜血迸射染红高粱的结尾整合,他追求的是“大沟壑、大抱负、大气象”,情节只是气垫。

《红高粱》是莫言创作的第二个台阶,一发表就好评如潮。张艺谋打算将它改成电影是1987年秋的事,那时他在帮吴天明拍《老井》,演主角。牵线的是影协的罗雪莹,因为莫言自己不愿改剧本,就请影协研究室的陈剑雨与我合作。陈剑雨是我在《人民文学》的同事向前的丈夫,他们的女儿,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雕塑家向京。张艺谋的习惯是先侃剧本,在我当时白家庄二十多平方米的家里,张艺谋一次次从《老井》的外景地赶来,盘腿坐在我家沙发上,人精瘦,两眼放光,聊到兴奋处常常忘乎所以,眉飞色舞。他太喜欢小说中余占鳌分开密集的高粱,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我奶奶”,“四面八方都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这样的描述了。
当时聊得最激动的是有关高粱的诗意表达,张艺谋那时很推崇日本一个导演一部拍芦苇的片子,我们一起用我家的录像机看过那片子,那种暗暗的光,风吹芦苇柔软摆动的绿美极了。张艺谋说,最后打仗的戏必须简化,“因为没有好的烟火师,八一厂就那些人,就那么几个炸点,绝对拍不出壮观的场面”。所以,一定要有大片大片,漫山遍野的高粱。我记得,罗汉凌迟怎么表现,当初讨论很多。谈得最激动是,罗汉死后,要让日本骑兵拉着石碾,把漫山遍野的高粱全部碾成绿泥。然后,大雨倾盆,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些被碾倒的残缺的高粱红了,那首歌唱起:“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这是小说里任副官教唱的歌。

但张艺谋后来到高密、东北、内蒙古去找外景地,走了一圈回来说,真是到处都找不到莫言小说中那种高粱的感觉,哪里还有那样大片大片,又高又密的高粱呢?不用说,大场景于是被否定了。据说,他最后在高密,只种了几十亩的高粱,只能拍局部的感觉。这部电影的投资,据说只有八十万。那是张艺谋的创业期。八十万,现在想,真是不可思议。
《丰乳肥臀》可能是莫言篇幅最长的小说,推动创作的是他母亲去世。在悲痛中,他要讴歌一个博大傲立的母亲为寄托,因此,56万字只用了83天,1995年春写完初稿,改了三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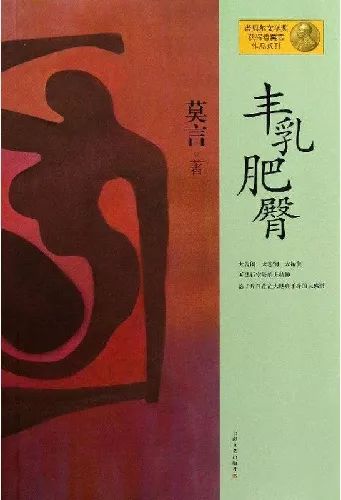
我是把《丰乳肥臀》与陈忠实的《白鹿原》放在一起,看作反映波澜壮阔的百年中国的两部史诗的。两部小说,都是五十多万字篇幅,沉甸甸,一部写陕西,一部写山东,映现百年中国,都极具代表性。写百年中苦难,回避不了外族入侵、兄弟相戕;回避不了前因后果,自己酿就的各种苦果。不同的是,陈忠实以质朴、雄浑的写实,塑造了一个白嘉轩,一个鹿子霖,两人斗了一辈子,写透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莫言则以象征的夸张,强调因果交缠的苦难,在男性家长缺失的前提下,讴歌一个在苦难中茹苦含辛,维系家族生生不息的母亲。“丰乳肥臀”是生殖力,农耕社会家族枝繁叶茂的基础。不“丰乳肥臀”,就不足以喂饱、养大、呵护这么多的子孙,所以,它是坚毅而旺盛的生命力的象征。母亲的胸膛就如敞开的广袤的大地,她不是现实中的母亲,莫言生活中的母亲,其实很瘦小。
莫言其实是夸大了生殖对母亲造成的苦难,来写母性之伟大。传统中国,传宗接代是女子的第一要务,因此,小说中聪慧的鲁璇儿一嫁到上官家,就变成上官鲁氏,没有了自己,只剩下维系上官家繁荣的职责。有意思是,这部小说中没有父亲:上官寿喜没有生育能力,寿喜的父亲福禄也只有他这一个儿子,于是,上官鲁氏要繁荣上官家,就只能借种:从姑父到土匪、江湖郎中、屠夫、和尚。
莫言塑造了一个质朴、坚忍又内在刚烈的母亲。成为生殖机器,接受一个个女儿的选择,接纳她们扔下的各种身份的孩子,她都是无奈。一介草民,她无力改变一切,只能承受一切,将绳深嵌在皮肉里,拉着家这辆破车,不断躬身前行。她说:“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地死,一茬茬地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这种活下去,且要记住的质朴,使她在战乱中推着木轮车,两边篓子里都坐着孩子,“两只小脚在冰雪中成了两个小镢头”;三年困难时期偷将豌豆吞进胃里,回家再吐出来喂活“鹦鹉韩”的描写,格外感人。母亲的光彩,尤其展示在那个大叫着“我要找我的孩子”,昂首走向磨坊的形象中。她顶着马排长的枪口,打了他一记耳光,轻轻地问:“你有娘吗?你是人养的吗?”在射来的子弹中,拔开了大门的插销。
莫言是以体量确立作品的重要性。他至今为止创作的长篇,体量最重是《丰乳肥臀》与《生死疲劳》。两部呕心沥血之作,论篇幅,《丰乳肥臀》排第一,《生死疲劳》少近十万字。论容量,《生死疲劳》的密度可能胜过《丰乳肥臀》,其中隔了十年。跨度上,同样写半个多世纪,《丰乳肥臀》的线性叙述,到《生死疲劳》变成一个轮回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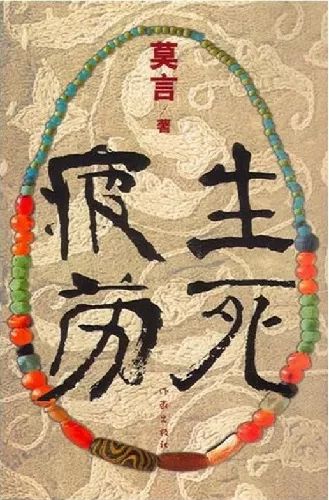
这部小说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讲1949年土改,地主西门闹被枪毙后,一直在畜生道轮回:从驴变成牛,牛变成猪,猪变成狗,狗变成猴,经猴才变成大头婴儿“蓝千岁”。之所以一直在畜道,是因为他总喊冤,不愿忘却痛苦与仇恨。本来,投胎前,喝“孟婆忘魂汤”就可忘记一切,但他拒喝或说那汤于他没有作用。他沉湎于过去无法新生,于是只能停留在“西门闹”的情境中。小说第四部《狗精神》的结尾,阎王问他:“现在你心中还有仇恨吗?”阎王说:“我们不愿让怀有仇恨的灵魂,再转生为人。”所以,就让他再转一次猴,“把所有仇恨发泄干净,再重新做人”。这是有关轮回,一个很深刻的角度。《生死疲劳》是莫言获诺奖的,一块决定性的基石。
《蛙》是莫言至今为止的最后一部长篇,写成于2008年,在《收获》发表后,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莫言给这部小说写的后记标题是“听取蛙声一片”。这是辛弃疾西江月词中的句子:“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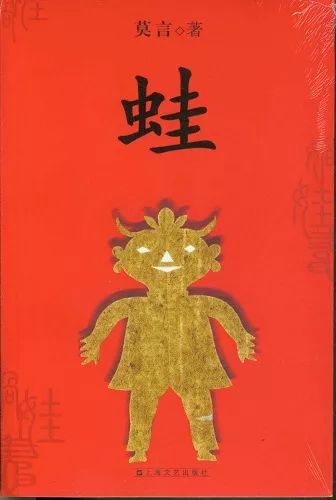
以这首词读这部小说,故事若放在词意中,会增添怅然悲伤。这部小说写农村粗暴推行计划生育酿就的悲剧及时过境迁后的荒诞。莫言是以蛙写娃,塑造了一个传奇的姑姑形象。他在后记里说,生活中,他确有一位妇科医生的姑姑,接生了数千婴儿,亦有“为数不少婴儿,在未见天日之前,夭折在她手下”。莫言借此姑姑承载计划生育这样的大事件,以蛙与女娲的“娲”为意象。
2012年,莫言以他三十年辛勤累积的辉煌成就获诺贝尔文学奖。我计算一下,从1981年发表第一篇习作到2012年获奖的三十一年,他写了约六百万小说,三百万字散文随笔杂文,总计九百万,在中国新时期作家中,累积篇幅之多,题材面之广,整体所具之深度,获奖是他辛勤的馈赠。他在三十年里走了别人可能要用五十年走的路,是实至名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