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忆年轻时,最喜欢的俄国作家不是托尔斯泰、雨果,而是屠格涅夫。书也“不是白读的”,从此她对深爱的人们,绝不放下利他心。
“读书就是这样,把喜欢的东西留下来,不喜欢的、看不懂的东西就放到一边,等待将来的日子去认识,好像反刍似的。”
本文摘自王安忆新书《小说六讲》,内容为2015年她在香港城市大学公开课上的讲稿,原标题《文字里的生活》。
01
童话与悖论
我想先从我的阅读生活来与大家分享我的成长经历。我似乎回想不起我是怎么学习识字和阅读的,好像生来就会了,阅读对我来说很自然,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就看见了文字。我的生活似乎从来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实际当中度过的,就是吃饭、睡觉、和父母相处、和小朋友一起玩耍;另一种生活则是在文字里,它给了我一个另外的空间。
我初始的阅读,大都是童话和民间传说。有一个童话故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故事讲述一个勇士受到上天的指令,让他去捕捉一只玉鸟,于是登上冒险的征途。上天以很郑重的语气派遣他,他就以为这次出行会很困难,艰险重重。想不到一路顺风顺水,很快就到达了玉鸟所在的宫殿。宫殿的门敞开着,也无人看守。进到深处,玉鸟独自立着,丝毫没有反抗,顺从地让勇士捕捉在手。玉鸟对勇士说:“我可以跟你走,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给你讲故事,你听了我的故事不能叹息,你一声叹息我就飞回去了。”于是,勇士就松开手,玉鸟立在他的肩头,往前走去。玉鸟讲了第一个故事,勇士忍不住发出叹息,玉鸟就飞回去了。勇士返身抓回玉鸟,再一次上路,玉鸟讲了第二个故事,勇士又叹息了。玉鸟飞回去,勇士回去抓,第三个故事开头……来回反复,一直到第九次,第九个故事,勇士没有叹息,方才成功捉到玉鸟完成上天的任务。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故事的具体内容,既想不起玉鸟让勇士叹息的故事,也想不起最后勇士不叹息的那个,可是它的结构却深印在我脑海。人的记忆很奇怪,像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选择,安排你记住什么,忘记什么。也许就是玉鸟故事中被我遗忘的内容的部分,从此变成一个逼迫,逼迫我不断地想象故事,使人叹息、叹息、叹息到不叹息的故事。人家的故事忘了,只有编自己的故事。
还有德国的《格林童话》,其中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个力大无穷的傻子。有一天,他跑到邻国去,看见城门上贴着告示,因城堡出现怪物作祟,很多勇士信心满满地进去,不是落败而逃,就是被怪物吃掉,没有一个人成功征服怪兽。国王非常不安,于是发出公告,许诺说谁能征服怪物,夺回古堡,就把公主嫁给他。这种模式的故事有很多,包括意大利歌剧《图兰朵》和中国戏曲《西厢记》,只是结尾各不相同,《西厢记》是老太太毁约了。这则童话故事则很朴素,傻子斩杀怪物,天下太平,国王立刻兑现承诺,把公主嫁给他。公主对他也没什么大不满,并不觉得他傻,只有一样使公主纠结,就是他不懂得害怕,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怕得发抖。公主有一个很聪明的宫女,就像莺莺小姐的红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严冬寒冷的早上,凿开河上的冰,捞了一桶鱼,提到卧室,把傻子的被子掀起来,一股脑浇在他身上,傻子不禁浑身战栗,大叫道:“哎呀!我知道什么是发抖了!”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的生活。

德国童话作家格林兄弟(雅各布·格林、威廉·格林)
小时候,只觉得故事有趣,后来想起来,这有趣里藏着许多隐喻:为什么公主把懂不懂得害怕作为一个人智商的标准,害怕和智慧有关系吗?过度诠释一下,又似乎有关系。中国人不是讲求敬畏天地吗?再有,如果这傻子是有智慧的人,懂得害怕,那么他就不可能征服怪物,娶到公主。这么一来,故事不是没有了吗?所以,他又必须是一个傻子。这是一个悖论,小说往往都是悖论。
童话是很有意思的。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收集编撰过一部《意大利童话》,其中一个故事说的是野兔和狐狸。有一天,狐狸在树林看见兔子快乐地跳来跳去。狐狸问兔子为什么那么高兴,兔子回说它娶了一个老婆。狐狸恭喜兔子,兔子说不要恭喜它,因为它的老婆很凶悍。狐狸说,那你真可怜。兔子说不,也不要同情它,因为老婆很有钱,带给他一栋很大的房子。狐狸再道恭喜,兔子又说不要恭喜它,因为房子已经一把火烧掉了。狐狸说可惜可惜,兔子说也别觉得可惜,因为它那凶巴巴的老婆也一起烧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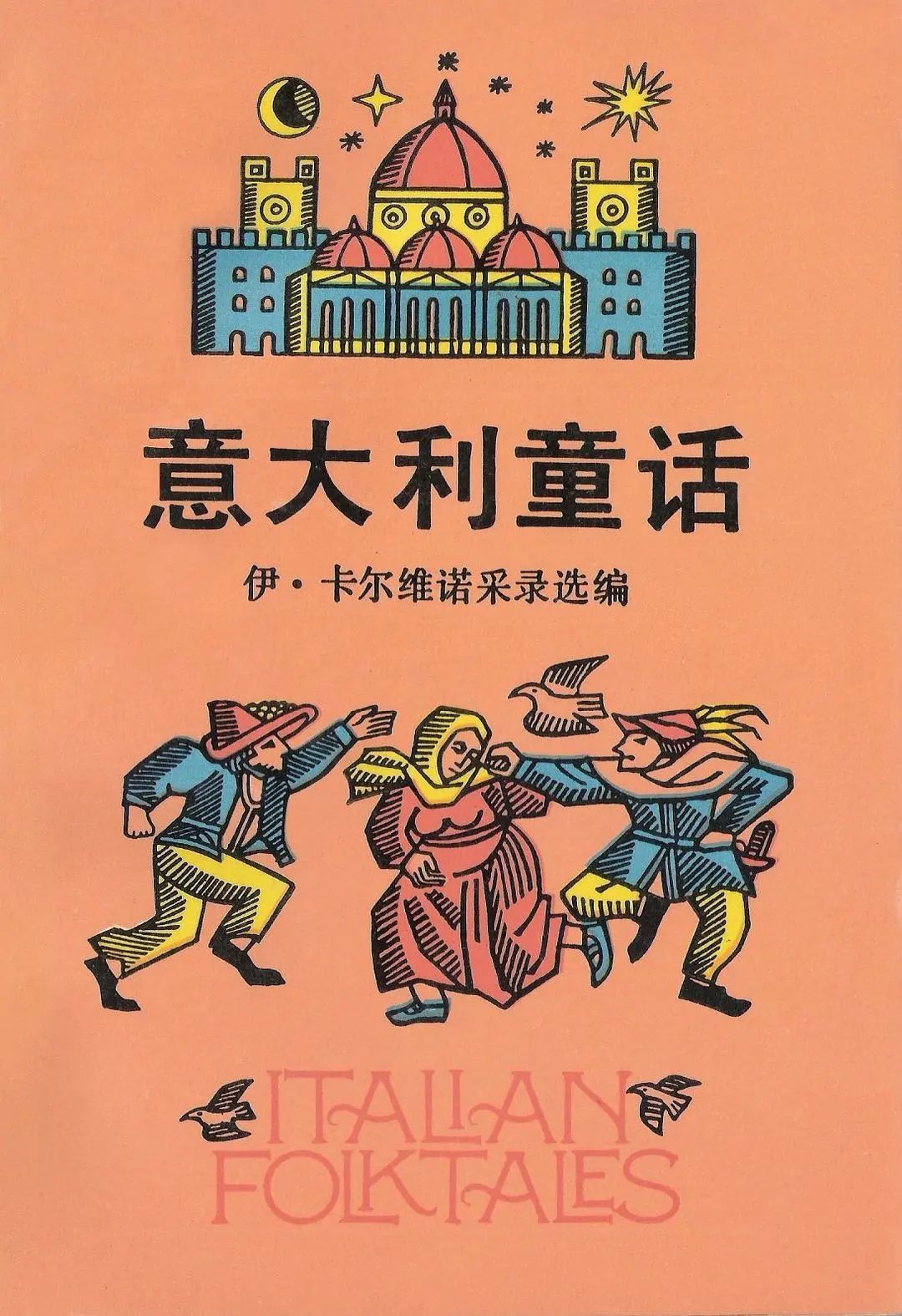
《意大利童话》, [意] 伊泰洛·卡尔维诺 采录选编,刘宪之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们写小说常常是这个样子。从起点开头,经过漫长的旅程走到终点,却发现是回到了原点,但是因为有了一个过程,这原点就不是那原点。所以我们又很像神话里那个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把石头推上去、落下来,再推上去、落下来……永远在重复做一个动作。但这一次和下一次不同,就是那句哲言:“人不会两次涉入同一条河流。”
幼年时看童话故事,觉得很好看。它建设了一个奇异的世界,是在现实生活里不可能发生的。慢慢地,成年以后,我对童话的认识似乎递进着、常想常新,今天想是这个样子,明天想又有不同的感受。童话故事看似是孩子的阅读物,但其实,它的意味和形式,隐匿在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阅读童话的经历实际上一直如影随形于我日后的文字生活。
02
校园小说
再长大一点,开始上学,对童话的热情转移到接近现实生活的阅读。对于一个学龄孩子来说,最恰当的读物莫过于“校园小说”。“校园小说”的模式来自苏联,把少年儿童的生活写得很严肃、高尚,因少年儿童是未来的英雄,被赋予实现人类理想的重任。例如说当时非常著名的苏联儿童文学小说家盖达尔,他的小说《铁木儿和他的队伍》里的铁木儿成为少先队员的学习模范,很多学校成立“铁木儿小队”,一种浪漫的激情充盈在我们的学校生活里。铁木儿系列的小说里,有一篇名叫《雪堡司令》,我至今还能记得。
故事讲述街上有两队小孩,分属对立的两派力量,其中一派就是铁木儿。就像我刚才说小时候两条弄堂的小孩争斗打架,而小说将这种小孩子的罅隙政治化了,因而也变得严肃。铁木儿领导的一班小朋友很正义,不欺负弱者,做好人好事,而他的对手是一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专门欺负小女孩。双方有一场战争,是争夺一座雪堡,即用积雪堆起来的堡垒,相持几日,胜负不决。有一天,铁木儿忽然带领队伍撤退,将雪堡让给“敌方”。原来,铁木儿从母亲口中得知,那个孩子的父亲在前线牺牲了。故事很动人,孩子们拥有着美好的品德,高尚的情操,并且抱负远大。

故事连环画《铁木儿和他的队伍》
分裂也是从阅读校园小说发生。我姐姐早我三年参加了少先队,我父亲当时还在军队,就给我姐姐寄来一本书作为她加入少先队的礼物。现在的礼物都是巧克力、游戏软件之类,那个时代的礼物也是严肃的。那是一本精装的书,书名已经记不清了,封面上是一个孩子的雕像,是关于一个苏联少年英雄的真实故事。他的名字叫莫洛佐夫,1918年出生,然后1932年他十四岁的时候,因举报他的富农祖父隐藏粮食被杀死。中国60年代的少年英雄刘文学,遭遇和他很相像,同是和侵吞集体财产的歹徒斗争,失去了生命。可是这个苏联小英雄莫洛佐夫和刘文学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男孩子所揭发斗争的人是他祖父,最终,他死于祖父的手里。于是,这故事就变得更悲惨,令人非常难过。因为这是他的至亲,血缘和阶级的敌对关系,给英雄的事迹蒙上阴影。多年以后的今天才得知,原来这位少年是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人物,是由一桩家庭的悲剧演绎而成的。我不打算评价这个事件,我只是想说当时阅读的忧愁。
其实这是一个先兆,预示着我逐渐分裂对文字世界的信赖。这本书让我觉得这世界的残酷,甚至比现实生活更不可依靠。很快,生活就进一步地加剧分裂的状况。1966年,“文革”发生,我早早结束所谓“学业”,到了农村。我身边携带的书,除方才说的农村小说集,还有一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是当代中国作家浩然所著,写的是人民公社新农村的生活。小说里的农村景象光明开朗,前途美好,有阶级斗争,可是不像那个男孩的故事那么混淆阴沉,而是黑白敌我清晰,感情就不会受到严峻的拷问。有爱情,没有私欲,建立在公德和理想之上;有新旧观念的较量,总是进步的胜出。宣传画上拖拉机行驶在光芒四射的田野上的图景,在小说里演化成生动具体的人和事。

《艳阳天》,浩然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和我所在的农村,在气氛上不大一样。我们村庄上,有一个富农的家庭,男人已经死了,老婆带着一儿一女度日。这一家人都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子,五官端正。女孩子很苗条,她的外号也很妙,叫“铁嘴”。她很会说话,言辞犀利,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几个来回就败下阵来。她不仅嘴厉害,干活也是一把好手。在我们那里,割麦子是用长柄镰刀,叫作“放大刀”。我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读过用大刀割草的场面,工具和姿势都类似“放大刀”,干活的都是男性壮劳力。可是,每每地,这个“铁嘴”女孩子都能进入“放大刀”的行列,她从来不落人后。
割麦的情景回想起来真有些戏剧化。我们的农民其实自有美学,割麦的季节里流行的装束:上身不穿衣服,光着膀子,肩上系一方白色的纱布,很彪悍也很俊美。在一列白披肩的队伍里,有一件花布衫,就是“铁嘴”。庄上人公认她是个人才,私下都为她惋惜,因为她的富农成分,一直没有寻到婆家。到我离开那个村庄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岁了。在农村,二十岁对于女孩,是个很可怕的年龄,很难有匹配的对象。她的弟弟也很秀美,同样娶不到媳妇。这一儿一女的婚事都是老大难。这是我在农村看到的阶级分野日常化地体现在个人命运上,和《艳阳天》里斗争的方式不同。书本里的世界固然美好,但却是简单的,它无法覆盖现实的复杂性,所以就变得脆弱。但阅读的经历,在我几乎成为信念,我并不因此而放弃,而是企图寻找出一个更有力量的文字里的世界。
我在农村里独自度过十七岁的生日。生日时,母亲送我一本小说叫《勇敢》,是苏联女作家薇拉·凯特琳斯卡雅所著,写的是上世纪上半叶苏联开发远东、建设共青城的故事,感情很激昂,合乎社会主义史诗的创作原则。母亲送我这本书是希望我振作,对目前的生活唤起一点热情,不要颓唐下去。当然她也知道书本和现实的距离是非常大的,可是除此,还有什么别的路径呢?我们都是容易被书本激励的。

这本书如果按照金克木先生的说法,就是“假”,但是小说确实写得很动人,这就是文字的能量吧!一群青年人在一片荒地上,从无到有建起一座城市是多么激动人心!乌托邦永远吸引着爱幻想的年轻人,但是成长会告诉我们,乌托邦的不可实现在于它的不合理和不人道。前面说过,那个少年英雄出生在一个伦理混乱的家庭,本来是个不幸的孩子,却被塑造成英雄。而《勇敢》所写的开发远东,正是在中国黑龙江边境,带有扩张的意图,结果也是失败的。在不断阅读和学习中,你会发现,在你非常投入、寄予很高理想的那个世界也是有谎言的。这是对我们提出的警告,警告我们,与虚假对立的不只是真实,还有诗。诗和真并列,当我们离开真实的时候,也许也与诗背道而驰了。
所以在写小说时,你要清楚你在建设一个怎样的文字世界。我庆幸我一生总能得到一些启迪,总有人或事引领我,让我走到相对正确的道路,不让我失足。大量混杂的阅读中,你其实很容易走上歧途;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不论错的和对的,具有一种自行调节的功能,纳入你经验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建立起明辨是非的可能性。生活中的缺陷使我情愿与自己的生活保持距离,远一点,书本就提供了这个机会。它们和我的生活可能没有一点相似,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有联系。
总的来说,我就是特别需要一个和我实际度过的世界不一样的空间。我不是要藏身逃避其中,而是它让我对我现实的遭遇有抵抗力。当然,它也许加剧我更不喜欢现实生活。要等到书本能帮助我度过这个分裂的时期,令我对正在经验的世界有一点喜欢,还需要很长的道路,还要经历更多生活,读更多的书。因为事实上,写小说的人如果不喜欢生活的话,是无法写小说的。小说和诗不一样,小说跟生活很接近,它是世俗的性格,是人间的天上。
03
爱情小说
让我再谈一下年轻时读的书。我常说我很喜欢托尔斯泰和雨果,但年轻时托尔斯泰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也不特别喜欢雨果。我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这个名字对你们年轻人来说可能很陌生,因为俄国文学不是今天的时尚。在我年轻时,我其实不能完全看明白他的小说。小说里俄国的政治背景,知识分子的苦闷,思想没有出路,那些更深刻的内容我不怎么了解,留在记忆里的印象是模糊的。读书就是这样,把喜欢的东西留下来,不喜欢的、看不懂的东西就放到一边,等待将来的日子去认识,好像反刍似的。于是,我就只看到爱情的部分。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总是有爱情,而且是不幸的爱情,年轻人多不喜欢一帆风顺的爱情,而是受爱情的悲剧吸引,年轻人总是伤感主义的。

俄国作家伊万·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的爱情故事都很伤心。在《初恋》里,一个年轻的男孩子爱上一个成年女性,爱得非常非常深。这份爱里,不仅有情欲,还有成长的渴望,希冀进入成年人的社会,和这个社会平等地对话。这个女人很美,很温柔,而且似乎也知道他的钟情,有一些微妙的回应。结果却是,她爱着他的父亲,一个成熟、经历过生活、有家室妻儿的男人。这不仅是单纯的失恋,而是一个失败的博弈,年龄、阅历、成熟度,和这一切有关的魅力的博弈。但是,还有一个更久远的博弈,这个博弈还未完,还未决出胜负,那就是未来的时间。他总有一天抵达父亲的年龄,父亲却永远回不到他的青春时代。所以,博弈的双方,父与子,都是痛楚的。屠格涅夫小说里有一个父与子的核心关系,他有一部长篇名字就叫《父与子》,可我注意不到,只看见爱情,因为自己也正处在蜕变的年龄,爱情对成长具有启蒙的意义。
读屠格涅夫的小说真的不是白读的。慢慢地,我们就建立起一种道德美学,那些深情的爱人们,并没有放弃利他心。虽然爱情是自私的,但是知识分子的人性理想约束着他们,使他们保持对爱的更高尚理解,悲剧就是在这里发生。屠格涅夫所写的故事和我阅读时经历的生活完全不同,他笔下的人和事,于我的处境称得上奢侈,但为什么我能够从中得到慰藉和启发?可能是有一个秘密通道,可能是青春,可能是对爱情的向往,也可能是成长的需要。
这大约可说是阅读生活的真谛,你和某一本书——不知是哪一本,会有一个秘密通道,就是这个秘密通道,令你在书中遇到知己,能和这本书邂逅,就是幸运。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共十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一部很好看的长篇小说。傅雷先生译的中文版,分成四本,“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得来第一本,里面包括前三卷。这前三卷,恰是人物从幼年到少年走向青年的成长过程,每一阶段都有一段爱情。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女性读者来说,非常令人激动满足。
第一段的爱情是小狗小猫式的,女主角叫弥娜,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钢琴课学生。他是一个穷孩子,有着音乐天赋,从小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除了在宫廷乐队演奏,还要教钢琴帮补家用。弥娜的母亲,一个孀居的贵族夫人,很慷慨地聘用他做女儿弥娜的钢琴教师。弥娜是个任性的女孩,出身优越,吃穿不愁,妈妈又宠着她。起初她看不起克利斯朵夫,因为他生相粗鲁,穿着简陋,不讲卫生,仪态也缺乏教养,所以对他态度相当傲慢。克利斯朵夫是公认的神童,也不买她的账,师生关系就很紧张。可是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把形势整个地扭转了。这一天,小老师指责学生弹了一个错音,弥娜不承认,用手指着乐谱说就是这样的,克利斯朵夫凑近看乐谱,看见的却是少女花瓣儿般的小手,完全是无意识地,他在那手上吻了一下。这一个冒失的举动,把两个人都吓到了。争吵平息,琴课继续,但心情就此搅动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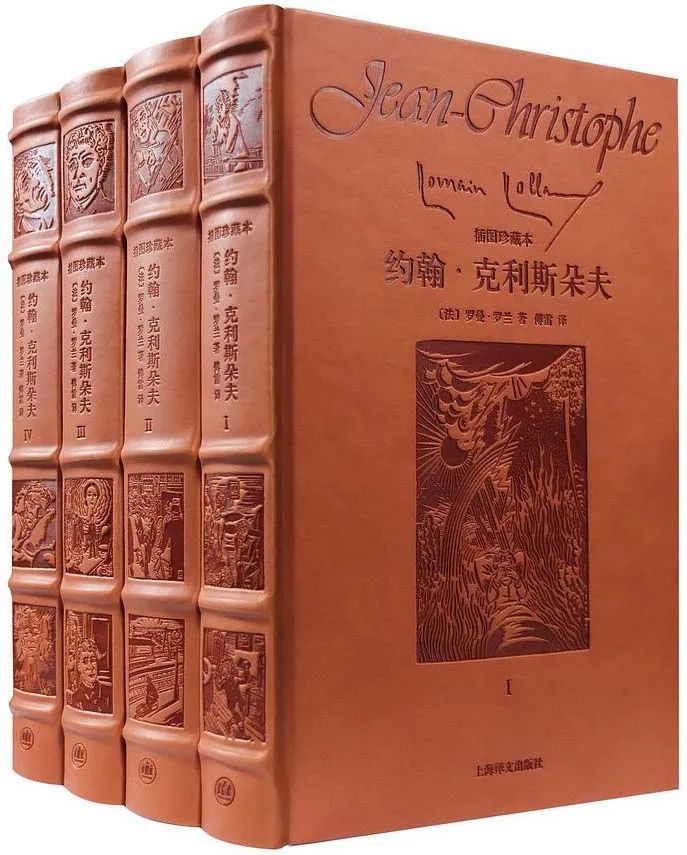
《约翰·克利斯朵夫》, [法] 罗曼·罗兰 著,傅雷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弥娜生活很简单,又没到进入社交圈的年龄,成天无事可做,难免胡思乱想。克利斯朵夫的这一吻,给了她新发现,原来她已经被这个男孩深深地爱上了。爱情遮住她的眼睛,再看克利斯朵夫,他的每一事每一物都变得可爱,钢琴弹得好,才华横溢,他的粗鲁只不过是男子气概的表现,他的破衣烂衫则是艺术家的风格,连他长相都变得英俊起来。克利斯朵夫呢,也以为自己其实早已经爱着弥娜,彼此的敌意不过是爱人之间常有的小别扭。于是,双双陷入情网。这一段爱情很快就被弥娜的母亲看在眼里。她是一个雍容大度的女性,她赏识克利斯朵夫的才华,但也明白他所属的阶层和她们不同,他和女儿之间只是孩子的游戏,一个不恰当的游戏。所以,就不要继续发展,而是及时收场,她带着弥娜离开了。
之后,克利斯朵夫遇到萨皮纳,展开了第二段爱情。年轻人对爱情的想象是概念化的,所以萨皮纳的故事让我有一点不满意。第一,她比他年长,是结过一次婚带个孩子的小寡妇;第二,她出身不怎样,既不是公主,也不是灰姑娘,而是个老板娘,开一间针头线脑的小店,显然缺乏女主角的浪漫色彩。还好,他们爱情的发生比较有戏剧性。他跟着萨皮纳去乡村参加亲戚的婚宴,郊游和歌舞制造了一个民间的欢场,暗中萌生的情愫迅速滋长起来。
因为大雨留宿小旅馆,他们隔着薄薄的墙,一举手把门推开就打破通道。两个人都知道墙那边站着对方,等待对方下手,可是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最终蹉跎了时机。这个结局满足我们对爱情的悲剧想象,而当过后再读小说,方才理解,要使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人,需要经过许多磨炼,和弥娜只是练手,仿佛过家家式地模仿成人关系;到了萨皮纳却是情欲露出水面,这不仅意味外部的生活在进展,更是内部——即身心发育成熟。
第三段爱情更加使我不高兴了。阿达是个粗鄙的女性,在一间帽子店里做店员,这个就更世俗了。她和克利斯朵夫并没有经过任何精神上的交流。和弥娜有钢琴课,萨皮纳有船上的合唱,阿达虽然也是邂逅于郊游,同样进了乡村小旅馆,但却是刻意安排,目的明确,迅速地上了床。这对于我们的道德美学、禁欲教育,最重要的是,罗曼蒂克的爱情憧憬,都太庸俗、太暴露。最令人失望的是,克利斯朵夫对此非常满足。那时候,我们只有第一本,之后的三本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拿到。多年以后,阅读全书,原来还有安多纳德和葛拉齐亚在等着我们。这时候,我们的阅历和阅读,已经积累到可以更尽情地享受其中悲怆的诗意了。就仿佛,和书中人物克利斯朵夫共同成长起来。

《约翰·克利斯朵夫(1978)》剧照
现在再读这本书,我最喜欢的段落恰恰是我之前不耐烦、急切想跳过的段落。例如,克利斯朵夫进入反叛的阶段,无论生活、爱情,还是音乐,都看不见前途,看不见意义,他憎恨他的环境,甚而至于他的民族和国家。他到犹太人家庭中寻找异质文化,又投到法国女歌手怀抱,希望汲取新鲜的生机,他到民间爱乐者的群体里,试图回溯音乐的原始性,却总是以失望告终。最绝望的时候,因为一个意外,卷入治安事件,只得离开家乡,流亡法国。在仓促登上的火车上,他朝着巴黎的方向,喊道:“救救我吧,救救我的思想!”到了巴黎以后,他发现音乐就像一个大工场,遍地都是制造和弦的店铺,无处不在。可是他还是找不到真正的音乐,他的思想还是得不到拯救。他到文学里去寻找,到社交圈里、爱情里去寻找,依然不得要领。最后,他生病了,滞留在廉租的公寓顶楼里,身边是庸常的小市民,琐细的日常生活,却感觉到有一种艺术精神在悄悄接近。后来,他邂逅安多纳德的弟弟奥里维,他们七天七夜足不出户,谈论法国、德国、民族、人类、革命……
这些章节在年轻时候被视作累赘,草草掠过,现在却觉得精彩极了!非常感谢傅雷先生,他翻译得那么好,真是一场文字的盛宴。据法国文学的专家说:“傅雷先生可说重写了这本书。在法国文学中,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影响远不如在中国,这应该归功于傅雷先生的再创作。”有时候,一本书,在你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营养,成为人生经验之一种。
《简· 爱》也是那时我喜欢读的一本书。我读《简·爱》是在“文革”的黯淡日子里,那故事远离现实,遥不可及,它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幸和不幸都是有趣而且有意义的。当我读过许多书以后,再看《简·爱》,难免觉得简单了。爱和自尊,经过跌宕起伏的波折,最终保持圆满的结局,过于甜美,近似类型小说。但是,正因为此,它滋养了我枯乏的生活,缓解了我的苦闷。

《简爱(2011)》剧照
阅读令我的生活变成两个世界—实际度过的生活和想象的生活,两者的关系我很难解释。它们好像是并行的,甚至互相抵触,但它们似乎又是有交集与和谐的,我站在书本里看实际的生活,同时,又在实际的生活里观看书本里的。它们之间相隔着距离,这距离开拓了我的视野。

本文节选自

《小说六讲》
作者: 王安忆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世纪文景
出版年: 20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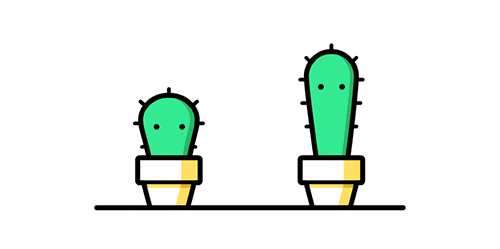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