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里,大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绪和感触:有“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深切思念,有“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及时行乐,有“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的时光飞逝……而在 《孟冬寒气至》这一首中,则写尽了一份最炽热的期盼与漫长的守护。
学者杨无锐在其新书《十九日谈》中,重新解读《古诗十九首》,在他看来,《古诗十九首》里可以“读到19个日常生活的故事,19个日常生活的神性瞬间”。其中, 《孟冬寒气至》这一首则是诗人笨拙而持久地坚守,这恰如当年王国维当年在文化衰落之际,蓦然回首重新发现的一种深厚生活。
《孟冬寒气至》的仪式,是对一封信的珍视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
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
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
《古诗十九首》里最好的诗,都写某种无须回报的隐忍和决绝。一个人决定担起所有重担,才有那种隐忍和决绝。等待、盼望、记忆,全都无比沉重。可是,总得有人把它们担起来。选择担荷的人,都是孤胆英雄。没有他们,爱与生活将会分崩离析。到那时,所谓世界只剩下刻薄寡恩的丛林故事。
《孟冬寒气至》可以和《庭中有奇树》《涉江采芙蓉》《客从远方来》构成一组。它们都写不能相见的相思,都写一个思念者为了守住思念,创造了美丽的仪式。《庭中有奇树》的仪式,是为远方人折下一朵绝艳之花,让自己馨香盈怀袖。《涉江采芙蓉》的仪式,是因为心怀故乡,而在异乡涉江采芙蓉。《客从远方来》的仪式,是把来自远方的锦绮裁成锦被,绣上鸳鸯,一针一线,都是在分离的无可奈何里讲述重逢、相守的希望。《孟冬寒气至》的仪式,是对一封信的珍视。
年轻时读诗,总喜欢往深处僻处想。读到“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可见三年来再无第二封信到来。由此推想开去,可见寄书之人的健忘。信上不是写着“长相思”“久别离”么?何以从此再无嗣音?可见寄书之人的客套,乃至虚伪。这么一路想下去,就觉得那个“置书怀袖中”的诗人真傻真可怜真天真:他竟不知自己的深情是唐捐了?他难道真以为思念换来的也是思念?他难道从没想过,自己的思念指向的可能是虚无?想到这儿,就觉得没什么好想了,干脆把诗扔到一边。年轻人,喜欢“聪明”“深刻”的东西。《古诗十九首》里的诗人,太厚道,厚道的人总是显得不太聪明、太不深刻。

后来,多少见了些世面。见了些世面的意思是,在书里见识了往昔时代的刻薄寡恩,在书外见识了这个时代特有的刻薄寡恩。刻薄寡恩式的聪明,惯于发现、剖析、审判世界的恶。惯于指控世界之恶的人,除了可以陶醉于自己的深刻,还可以一劳永逸地替自己卸下爱世界的责任:既然没有什么真正的、纯粹的美好,那也就没什么东西配得上我的爱。
我刚刚写下一段晦涩的话。我只能用这样的句子描述我见过的那些“世面”。到处都能看见那种刻薄寡恩式的聪明。比如在我熟悉的大学里,老师极其聪明地为学生分析一首诗,分析的目的,是让学生丧失爱一首诗的能力。因为老师自己就不爱。我受到的最初的诗歌教育,就来自这样的老师。从他们那里,我学到的不是读诗,而是熟练使用社会学术语、经济学术语,以及各种版本的阶级斗争术语。我养成的阅读习惯,就是用各种术语把诗大卸八块,然后发现里面空无一物,然后冷笑一声,转向下一首。不只是对诗,对整个世界,我也习惯于拆解。说实话,当一个人的头脑里装满了那些术语,除了拆解,他几乎无事可做。拆解的效果是,所有那些跟爱和正义有关的事情,都失去了光彩。无论在哪里听到、看到、读到这类事情,我都能凭借拆解技艺,一眼看穿它们。在大学里,人们把这种看穿称为深刻。看穿,会给人带来解放感:既然没人会尊敬被自己看穿了的东西,既然没什么东西没被看穿,那么,也就没什么东西值得尊敬、爱。不能爱,不能尊敬,不是我病了,而是世界病了。
这就是我所见过的“世面”。我就带着这“世面”赐给我的教诲生活了好些年。那些年里,我到处运用刻苦习得的刻薄寡恩的聪明,努力看穿一切。慢慢地,我觉出哪里不对劲。我引以为傲的“看穿力”,可能只是让我看不见任何东西。打个比方吧。一双可以看穿一切的眼睛,就像一部 X 线胸透仪。带着这样的眼睛走进人群,我看不到或美丽或丑陋的男人、女人。我根本就看不见人,只能看见一堆堆骨骼、内脏、血液和油脂。骨骼、内脏、血液和油脂,或许也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但我错过了更加真实的事情:那些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

我看穿了自己的“看穿力”。从那时起,我厌倦了刻薄寡恩式的聪明。我试着重读那些厚道的诗,比如《古诗十九首》。我发觉,诗里的厚道非但不乏味,甚至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勇猛。每一个厚道的句子背后,都有一位厚道的诗人。每位厚道的诗人似乎都要守住些什么。见过很多“世面”之后我才知道,守住什么,远比看穿什么更需要勇气。我的经验告诉我:守不住想要守住之物时,人们往往选择看穿它;疲弱贫血的人,特别容易看穿一切。
《古诗十九首》里,没有看穿者,只有守护者。《孟冬寒气至》的诗人想要守住什么呢?他想守住一个好消息。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这又是一个孤独的愁苦的人,又是容易让人孤独愁苦的冬夜。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就在孤独愁苦的时候,他收到一封信。信,让这个孤独愁苦的人知道自己仍然活在爱里。“长相思”“久离别”,这六个字告诉诗人,在用孤独和愁苦包裹着他的时空之外,还有跟他有关的爱意。对他来说,这是个莫大的好消息。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于是,这个孤独愁苦的人,就认真守住这个好消息。他无比珍视这信。珍视的方式,不是紧锁密藏,而是贴身携带,时时展读。只有这样,那个好消息才是永远鲜活的好消息,跟他有关的好消息,而非陈年往事,或虚假幻觉。这个在孤独愁苦的时候收到好消息的人知道,守住这个好消息,就是对它的回报。
《孟冬寒气至》就是这么简单的诗。一个人,用三年守着一个好消息,或许还会一直守下去。其实,只要他足够“聪明”,本可以在几秒之内“看穿”那个好消息。
王国维:先是望向彼岸,终于回到生活
1927 年 6 月 1 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关于静安先生的死因,报纸坊间流布着各种传闻。有人大谈他与罗振玉的私人恩怨,有人剖析他对革命、进步的恐惧,有人赞颂他对清朝皇室的忠诚。不久,陈寅恪发表了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序言里,他斩截地说,静安先生的死是殉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6—11页)
依照当时流行的新闻腔调,静安先生通常被刻画成木讷守旧的老学究。没人敢对他的学问说三道四,但人人都觉得有资格嘲笑他的胆怯,惋惜他的愚忠。陈寅恪根本不理会这些自作聪明的下流评论。他直接指出了静安之死的精神意义。当时的汉语知识界已经贫瘠到这种地步:人们几乎没有能力理解党派斗争、阶级革命、美元卢布、舰艇坦克之外的任何事情;人们不能理解更不能容忍任何精神事务、精神痛苦。陈寅恪说,静安先生的死,恰恰是一桩超出流俗心智理解范围的精神事件。

王国维
静安先生的忠与殉,当然与清皇室有关,但不止于此。一个存在了几百年的王朝固然真实,一种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化、信仰同样真实。对于关心军队和选票的政客而言,前者才是唯一的真实。对于活在文化、信仰之中并且受其塑造养育的人而言,无形的文化、信仰远比有形的王朝更真实。两种真实,几乎不可能放到一起比较、讨论。在一些人眼里真实不欺的事情,在另一些人眼里只不过是蠢话、谎言。当时的知识氛围是,从学术领袖到半文盲,人们争抢着戳穿“中国文化”,把它拆解成蠢话、谎言。层出不穷的戳穿、拆解出现于高文典册,也充斥于街头小报,构成了当时的智力狂欢。偏偏,陈寅恪说,那个似乎早已被戳穿的文化是真实的。只不过,这种真实不会对所有人显现。唯有“为此文化所化之人”才能真切地看到它,珍重它,疼惜它。静安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稍稍了解静安先生生平的人都知道,早年的静安先生并非木讷守旧的学究。
35 岁之前,静安先生醉心西洋哲学。出生于 1877 年的静安先生,也和他的同代人一样,有过但从域外觅真理的经历。只不过,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关心的,是所谓“富强”之真理。静安先生的独特之处是,“富强”之外,他还关心灵魂问题。他说自己少年时代多病多愁。他希望找到某种哲学,可以安顿一颗敏感愁苦的心。在他看来,哲学若与心灵无涉,充其量只能算是政治学、社会学。正是带着心灵的饥渴,静安先生发现了康德、叔本华,尤其是叔本华,一读就是十年。
1911 年,静安先生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就在这一年前后,他的学问发生了著名的转折。此前,他是爱谈善谈的哲学青年;此后,他成了整理古籍古物的沉静学者。关于这个转折,同辈人张尔田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忆余初与静庵定交,时新从日本归,任苏州师范校务,方治康德、叔本华哲学,间作诗词。其诗学陆放翁,词学纳兰容若。时时引用新名词作论文,强余辈谈美术,固俨然一今之新人物也。其与今之新人物不同者,则为学问。研究学问,别无何等作用。彼时弟之学亦未有所成,殊无以测其深浅,但惊为新而已。其后十年不见,而静庵之学乃一变。鼎革以还,相聚海上,无三日不晤,思想言论,粹然一轨于正,从前种种绝口不复道矣。(《王国维全集》第 20 册,263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
至于转变的原因,今天已很难理清。罗振玉的劝说和引导肯定起了作用。更要紧的,可能还是静安先生的心灵世界发生了某种改变。他在写给沈曾植的信里提到了这个变化:
国维于吾国学术,从事稍晚。往者十年之力,耗于西方哲学,虚往实归,殆无此语。然因此颇知西人数千年思索之结果,与我国三千年前圣贤之说大略相同,由是扫除空想,求诸平实。(《王国维全集》第 15 册,第68 页)
……
每从蕴公处得读书疏并及诗翰,读“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之句,始知圣贤仙佛,去人不远。(《王国维全集》第 15 册,第69 页)
早年的静安先生,相信在此处之外的某个别处有一个真理,只要找到它,就可以安顿一颗不安的心。这就是他所谓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了找到那个真理,他上下求索,苦读苦思。正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人至中年,他发现所谓“真理”并非悬浮于世界之上的某个现成之物,“真理”不可能被找到、摘取,只能从生活中涌现。正因如此,不必执着于“真理”在西方抑或在东方。相似的“真理”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涌现,只要那些地方有过深厚的生活。所以他说:“西人数千年思索之结果,与我国三千年前圣贤之说大略相同。”静安先生的中年转折,可能与这个洞见有关。这个洞见的核心,是摆脱了对“真理”为现成之物的执念,也顺便摆脱了东西之争的执念。摆脱两种执念,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回到深厚的生活,领会时时涌现的活泼泼的“真理”。用静安先生的话说,就是“圣贤仙佛,去人不远”。当然,他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譬喻:“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关于静安先生的“三境界”说,已经有太多解读。我认为,他可能是用三句词表达自己的心灵转变:先是望向彼岸,终于回到生活。

《王国维全集》
作者: 王国维 著 / 谢维扬、房鑫亮 主编
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 2010-9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可能是中年静安先生收到的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让他得以暂时从青年时代的惶惑中抽身出来。中年以后的静安先生,仍然敏锐易感。但他不必再把自救的希望寄托于某一个人、某一本书。让他暂得安歇的,是一种深厚的生活。陈寅恪所谓的“中国文化”,就是这种生活的精神实质。深厚的生活,曾经切实发生过,也曾留下无尽的遗迹。整理遗迹,既是向那生活致敬,也是向那生活求援。为何要向它求援?因为当下的世界正在分崩离析。
学者时代的静安先生做的工作,正是向那种曾经涌现“真理”的生活致敬。他写《殷周制度论》,便是意在揭示那种生活中蕴含的精神价值。他的大多数论文,严谨、清晰、冷静,扫除高论、空谈。他用勤苦的工作护惜安阳、敦煌、居延的断简残编。因为哪怕一纸一字,都是灯火阑珊处那人的雪泥鸿爪。
静安先生特别喜欢沈曾植的一句诗:“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他经常劝说老前辈沈曾植多写点儿东西,写论文、写诗,都好。因为“诗”是“道”的纪念碑,也是“道”的遗迹。“道”崩坏,“诗”也必将崩坏。等到人们连纪念碑和遗迹都不知护惜的时候,“道”也将彻底被遗忘。静安先生用沈老的诗劝说沈老:为了值得护惜的“道”,也请护惜人间的“诗”。只要“道”不穷,一纸一简中皆有“诗”在。
前些年研读静安先生的著述,时常心生感慨。读到那句“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一下子想起《孟冬寒气至》。静安先生不就是那个在凛凛岁暮里孤苦彷徨的诗人么?正自孤苦彷徨,他收到一个“好消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为了守护这个“好消息”,他用了半生时光。“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他尽力护惜与那个“好消息”有关的一纸一字,岂止三年而已。终于不忍看它分崩离析,殉之以死。
再后来,静安先生的“愚忠”,就成了聪明的戳穿家们的谈资。那就是一个与诗无关的不堪的故事了。那样的故事,发生于没有好消息的凛凛岁暮,刻薄寡恩的凛凛岁暮。

本文节选自

《十九日谈》
作者: 杨无锐 著 / 刘鑫 绘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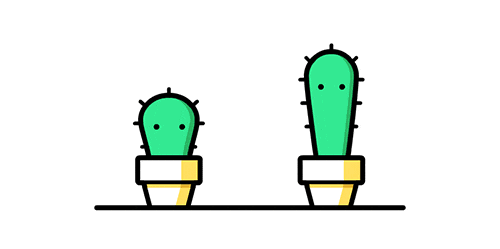
编辑 | 仿生斯派克
主编 | 魏冰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