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主人公们与卡夫卡、艾略特笔下的人物相似;张爱玲的阅读兴趣是维多利亚小说,如毛姆、赫胥黎;白先勇《台北人》的基本结构来自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主角名融合了两种文化……
以上观点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欧梵,他曾在北京大学胡适人文讲座上作五场讲演,内容经整理后于今年出版。本文从这本《两间驻望:中西互动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摘选部分,供读者进行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研究和细读。
1.
鲁迅和卡夫卡同代,但没读过他
鲁迅和卡夫卡是同一代人,1918年鲁迅写《狂人日记》,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和《审判》出版于1915年,主人翁也是一个狂人。当然鲁迅没有看过卡夫卡,卡夫卡当时默默无闻,刚刚在布拉格稍有名气,卡夫卡的文本没有进入中国的语境,好像茅盾提过一点,他真正进入中国的文学语境是在1960年的台湾,刚出版的《现代文学》第一期把卡夫卡作为专号,大力吹捧,是台大外文系的几个学生——特别是白先勇和王文兴——经由阅读美国学院批评家的文章看到的。
我们暂时不谈卡夫卡的文学渊源,如果再回看鲁迅的《野草》的话,你就会发现鲁迅的焦虑感,对于时间的焦虑感,正是《野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野草》我看了不知多少次,但初看时不知道怎么办。我写的那本鲁迅的书,实在糟糕,最糟糕的一章就是讨论《野草》的。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解读。我现在读来就有所感受,比如《影的告别》,大家都很熟悉,我认为影子的困境就是一种时间的焦虑感,就是一个时间的吊诡和两难局面。《野草》是一本散文诗,写于1924—1925年左右吧,同一个时期,甚至比鲁迅稍微晚一点,艾略特的那首诗The Hollow Men(《空心人》)出现了。《空心人》里面也有影子,形象和鲁迅的《影的告别》十分相似。我们可以证明鲁迅没有看过艾略特,可是两人为什么有这么惊人的相似?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英国诗人、作家艾略特(1888-1965)
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性只有一种,从欧洲传到世界各地,到了不同的文化里面产生不同的反应;也有学者认为有所谓多重现代性,中国有中国的,日本有日本的,因其传统而不同。我认为,至少在文化层面反应不同是真的,所以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日本开始有比较接近欧洲式的焦虑感,而中国似乎没有。如果有的话,就是少数敏感的作家,像鲁迅这种人。我们可以说,基本上,现代主义艺术的精髓在中国没有生根,或者是西方的现代主义在中国没有生根,但对于现代性的焦虑感在文艺上的表现,我认为中国绝对有,只是要看你怎么样来重新阐释它。问题是,这种焦虑感和“五四”以来的向前看的意识形态是截然不同的,当现代中国人的愿景是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开始用白话来统一语言,开始一步一步推进要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在这种前瞻性的思想推动之下,有什么好焦虑的?
2.
张爱玲的阅读兴趣是毛姆、赫胥黎
从文学上来看,我觉得如果说张爱玲受到一些西方小说启发的话,跟我刚刚讲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肯定她不喜欢乔伊斯,不喜欢卡夫卡,当时上海也看不到。她可能受到毛姆的影响。我记得有位上海的老先生来听我演讲,听完后他说,好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的句子在毛姆的哪部小说里看过,那些用词和意象,好像和毛姆很像。他的评论我一直记着,但没有时间求证。
所谓文学的读书品味,每个人都不同。张爱玲后来在美国那么多年,很容易接触到当时三十年代的西方左翼现代主义,特别是布莱希特,因为她的丈夫赖雅,就是布莱希特在美国的代理人,也是处理布莱希特遗产的人。很多布莱希特学者去访问张爱玲,但她不知道她老公做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张爱玲对现代主义完全没有兴趣。她的兴趣在哪里呢?维多利亚小说,或者说二十世纪初的维多利亚式小说,就是毛姆和赫胥黎。还有一些女作家,有一位名叫Stella Benson,是著名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后母,一位二流小说家,还是女权主义者,我没有看过她的东西。张爱玲的英文很好,她的可贵之处就是,在她的文风和文体里没有看到故意模仿西方的东西,她用的是从中国的通俗文学里面演变出来的她自己的文笔,所以大家那么喜欢她。
她的用词不是翻译性的。你看不出翻译的痕迹。你可以看到她用的意象,你如果拿她和毛姆的东西对照比较的话,或者跟电影对照比较的话,就很有意思。我举一个小例子,《倾城之恋》最后,范柳原在旅馆里面打电话给白流苏,突然说一句“我爱你”,过了一阵打电话问她:从你的窗子里看得见月亮吗?还说我这边窗子吊下一支藤花。这个场面是从好莱坞电影借用过来的。我最近看过一部老电影,故事说的是一个有钱的男人追求一个落难的小国公主,于是就在酒店里面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还唱起情歌。张爱玲厉害的地方是,如果说范柳原讲了一句我爱你就完了,没有下文,那么这段调情戏就没有意思了。可是她把这个场面处理得比那部影片还有品位,后来又故意引用《诗经》。这个是张爱玲厉害的地方。这是个小例子,以小窥大。

《倾城之恋(1984)》剧照
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张爱玲从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里面提炼出一种很特别的艺术视角,我在文章里面都提到过,她不是一位学院型的作家,可是她喜欢研究红楼梦,也吸收了很多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养分,这点大家都知道,可是西洋小说她也看了不少。我比较喜欢她早期的短篇小说,后来写的长篇我个人反而有一些保留。她的英文小说写得也不见得成功,最近出了两本《雷峰塔》和《易经》都不太成功,不是她的英文不好,而是因为她太急于给美国读者描写她的中国生活,反而引起一些文化上的误差,比如说她讲她在上海的大家庭里面那些丫鬟、亲戚的名字,都变成一种美国式的名字,有人叫兰花,有人叫菊花,我读来就感觉有点不太舒服,用现在时髦的理论说,就是有点“东方主义”了。不过她绝对是一位有才气的作家。我最近提出另一种观点:其实张爱玲是一位非常好的电影编剧家,她在香港写的一些喜剧的剧本,其中的对话绝对是和好莱坞电影有直接关系的,我是以一个影迷的身份提出的这个观点。在香港已经有人研究了,内地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兴趣。
3.
《傅雷家书》里有罗曼·罗兰的音乐观
现在还有多少人看过《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有多少人听说过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名字的?中国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有名的翻译家是傅雷。我因为最近在香港写乐评,认识一位年轻的朋友路德维,他跟我是音乐上的老友。他有一天突发奇想,说想看《傅雷家书》,因为《傅雷家书》里面讲到罗曼·罗兰的音乐观,于是他就开始研究傅雷和罗曼·罗兰,因而也带动了我的兴趣。他发现了一本很珍贵的小书,作者是茨威格(Stefan Zweig),是当时维也纳的一位名作家,也可能是奥匈帝国的最后一个文人吧,后来流亡到巴西自杀了。茨威格写过很多名人传记,这本《罗曼·罗兰传》早已经绝版了,我那位朋友竟然找到一个翻印本拿来给我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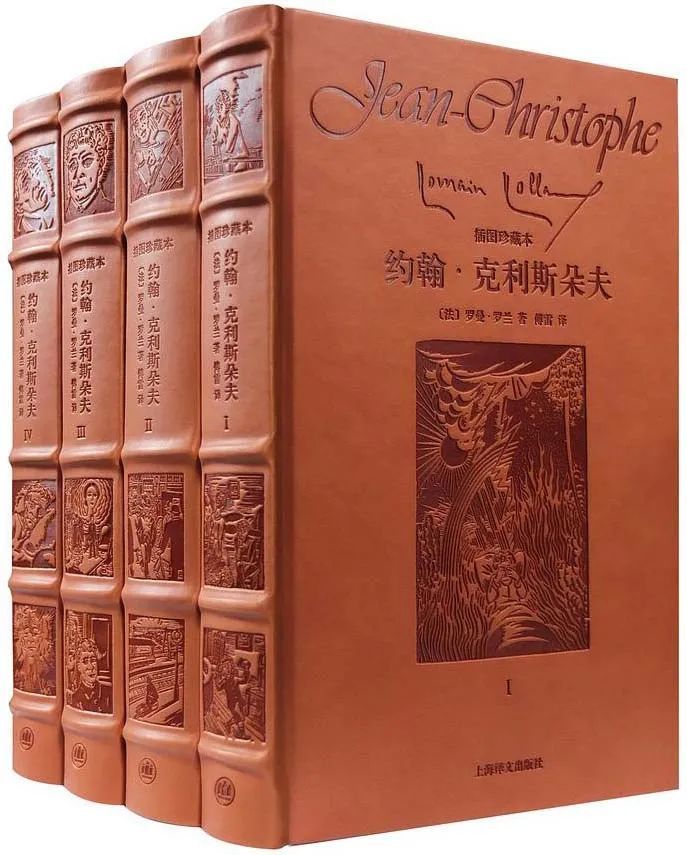
《约翰·克利斯朵夫》,[法] 罗曼·罗兰 著,傅雷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茨威格在书中大讲《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重要性。根据他的说法——我想他是代表二十年代欧洲知识分子共同的想法——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不只是一部音乐家的传记,也不只是一部讲天才艺术家的成长小说,而是说德国和法国这两种文化必须要互相交流,不能敌对,因为他们在文化上是同源的。如果大家看“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名字,他虽然生在德国,算是德国人,所以他的姓是Kraft,德文的原意是“力量”,然而他的名字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却是法文拼出来的。他在德国一个小镇长大,成为音乐家,后来到了巴黎,遇见一个法国人,叫奥里维,两人成了好友。故事的象征意义非常明显:德国人跟法国人成了好友,两个人代表了两种文化最优秀的品质。可是故事当然不止于此。
我记得在台湾念中学的时候读过这部小说,那时候只看内中的爱情故事,约翰·克利斯朵夫爱了好几个女人,可是到了最后那个恋爱故事我看不懂。原来他最后爱上了一位极有修养的意大利的贵妇,可是两人见面的时候都已经老了,所以完全是柏拉图式的恋爱,相对于轰轰烈烈的恋爱,两人更像是好朋友,我觉得很难理解。我猜罗曼·罗兰的意思是说,爱情不仅是肉体上的激情,而是一种心灵境界,当艺术把人的道德带到某种至高的程度的时候,真的是进入了最美好的境界。罗曼·罗兰认为可惜的是,这种境界现在欧洲文化里已经没有了,大家都为了欲望、为了金钱、为了战争而辜负艺术和人生。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4)
最近我又看了一遍《傅雷家书》,发现原来傅雷先生说他也看不懂这段故事,我们灵犀一线通,也是一个偶合。于是我不自觉地开始研究罗曼·罗兰和他的那个时代,从历史的角度开始追踪他的一生和他的著作。发现他写了几部名人的传记,特别是《贝多芬传》,也是傅雷翻译的。
4.
茅盾写工人经验,不如他写股票
《子夜》写股票写得非常精彩,写民族资本家和小布尔乔亚的知识分子,也写得非常精彩,甚至吴荪甫的年轻妻子读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都写出来了。当然第一章写他的老太爷从乡下到上海,看到大都市的五光十色的那一场戏,简直可以拍成电影,也已经拍成电影了。

《子夜(1981)》剧照
茅盾看过很多西方文学的书,对于欧洲文艺潮流很有知识。所以我想茅盾写《子夜》,一部分靠他自己的社会调查,但大部分是他从读过的欧洲左翼文学和文学理论中得来的资料和灵感,这个我没有时间来研究了。《子夜》里面其实并没有处理左翼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如果有的话,也不是那么精彩。当然你可以说在他早期的三部曲《蚀》里面反而有些描绘,记得第二部中有一位领袖自杀了,所以有人批评《蚀》里面有太多的虚无主义。
茅盾还是个书生。我觉得他写工人的经验不如他写股票。左拉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左拉的经验丰富。法国文学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就是写实主义,像巴尔扎克,他的小说就涵盖法国所有的现实,写过都市和农村。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产生一种社会调查式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后来传到苏联,发展成一种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写”。法国从巴尔扎克一直到左拉,从写实主义到自然主义,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左拉写得更仔细,好像把人物放在显微镜中来审视。他对巴黎和巴黎郊区的乡村很熟悉,至少从他的文章里面能看到很多。
中国的都市文学在三十年代其实不多,因为五四时期写的都是农村,知识分子大多来自农村,中国的都市和农村是连在一起的,只有上海是个例外。上海与其他城市的差别太大了,所以才会有这种刺激,产生了一些都市文学。我觉得反而曹禺的戏剧《日出》写得很精彩,把都市里的知识分子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最后把工人运动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写出来,但没有直接描写,直接面对就反而失去戏剧效果了。

《日出(1985)》剧照
5.
《台北人》很像《都柏林人》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了一门“现代文学经典”的课,选了《都柏林人》中的两个短篇,还特别讲《尤利西斯》的最后一段“摩莉的独白”,连续两三页全是意识流,没有任何标点,其实英文本身并不难。不禁回想到当年读过的乔伊斯,其实当年我根本不了解为什么我的同学那么喜欢乔伊斯。事后思之,我想他们崇拜的都是早期的乔伊斯,是写《都柏林人》的乔伊斯。

爱尔兰作家、诗人乔伊斯(1882-1941)
《都柏林人》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它究竟好在哪里呢?说来话长。我认为里面最精彩的一个短篇就是《阿拉伯商展》,情节很简单,讲一个小男孩偷偷爱上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有一天晚上,华灯初上,他突然看见小女孩站在门口,就第一次跟她讲话,问她:“你要不要去商展啊?我们一起去好不好啊?”那女孩说:“不行,我要在家里做祷告。”于是他就一个人去了阿拉伯商展,就是一个类似于游园会的地方,结果到了那里受人冷落,看到管店铺的那些人在那里互相调情,不理他,他拿着钱想为小女孩买一个礼物也没买成,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可是里面表现了什么呢?研究乔伊斯的学者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显现”(epiphany),一种抒情时刻的突然感受,就像那个男孩突然看到小女孩时的那种感受,有点宗教味,好像有某种神秘的东西显现出来一样。在乔伊斯前期的小说里面,他自己说处处要寻找这种有神秘味道的时辰,并把它用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当时看得简直入迷。你想想看,哪一个年轻的男孩女孩没有浪漫的幻想?从乔伊斯小说的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原来个人的感情和文学形式的艺术感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所以《都柏林人》中几乎每一篇都对我们有吸引力。
台湾有一位学者研究白先勇的小说,把《都柏林人》直接和《台北人》画等号,两个城市似乎可以神交,甚至也可以用后殖民理论来对照。那时候台湾就像是美国殖民地,而爱尔兰是英国殖民地;爱尔兰是一个农村社会,台湾也是一个农村社会;在爱尔兰用英语写作就像是二等公民,而台湾作家也有类似的感受。当然这种说法有点牵强,我们当时很容易认同一名爱尔兰作家描写的那种世界,可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做不到,就是那种非常强烈的艺术感,乔伊斯可以离开爱尔兰,后半生在巴黎和瑞士度过,依然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受到像庞德这种人的欣赏,而我们这些人,包括白先勇都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去美国留学,所以后来王文兴和白先勇都去了艾奥瓦大学的写作班,要圆他们的写作梦。

《台北人》,白先勇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先勇在美国写的两个短篇小说集,一个是《台北人》,一个是《纽约客》,这两本小说集的基本结构,我认为都是来自《都柏林人》。我想他可能看了《都柏林人》之后,感受到那种流离感,很多从大陆流亡到台湾的人都感受到的那种流离失所,他就把各种感受放进了《台北人》的故事里面。你看他的故事标题,也有“出殡”和“国葬”这类字眼,最后是讲一代人的死亡。还有一点就是,在形式上《台北人》也和《都柏林人》一样,是由互相连接的短篇故事合成的。这种结构在当年的美国文学中,似乎只有一本:Sherwood Anderson的Winesburg Ohio(指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有点相似,描写的也是一个小城,但没有文化沧桑的历史。
6.
诺奖承认的作家,不见得都伟大
我如果说中国没有伟大作家的话,那就得罪了整个八十年代的作家,如果说他们太好的话,我又觉得毕竟是没有真正伟大的作家。 当然你可以先来一个冠冕堂皇的名词,什么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定义是什么?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学了理论和方法,并不能保证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我个人坚决反对诺贝尔奖,因为文学的标准和尺度都不能完全客观,诺贝尔奖承认的作家,不见得各个都伟大,而且伟大这个词的定义也很难说。
我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伟大作品的条件》,特别提到构思的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讲,好的作家至少需要有两三样东西,一种是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一种视野,就是自己对于整个文学、对于整个国家和世界的视野。我觉得中国的作家太关心中国了,而对于国外的东西要么就是拼命地学,要么就是拼命地批评。其实国外并不只是英美而已,我当年最喜欢的是拉丁美洲的作家,后来一头栽进布拉格的文化,就是因为我喜欢捷克文学,特别是昆德拉,他们这些国家的作家,既有欧洲视野,又有自己的乡土情怀。中国当代作家中也有这样的观瞻的,像韩少功就是一个,韩少功很懂得西方文学,他翻译过昆德拉的小说和葡萄牙诗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作品。

韩少功
所以也许我可以这么说,伟大的作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被发现的,恐怕需要有一些积累,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起步,其实是在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真正开始有自觉的写作,那一代的作家真有不少好作品,各人有不同的写法,当然也有些人最近不大写了,像冯骥才,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受到他们那一代人影响的年轻作家也慢慢开始积累,现在我觉得有几位中国当代作家十分优秀,莫言就是一位,其他还有几位。这些作家都定位在乡土,这一点我是坚决主张的,就是中国的作家一定要定位在乡土,自己的乡土,可是同时也要有世界观瞻。世界观瞻这个东西比较难讲,我也有种感叹,现在全球化的好处就是可以到处旅行,可以到处吸收,可是到底吸收什么东西?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世界观瞻的话,应该是你到了一个外国的地方,第一件事是问你们这里有哪些作家,有什么文化,管你喜欢不喜欢,去找找,这才是世界观瞻,而不是先下结论:我的文化比你还强!强弱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作对比,这都无所谓,比较并不是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可是我觉得这种世界观瞻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反而越来越缩小了。

莫言
台湾很多作家都非常有才气,可是台湾现在也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不喜欢旅行了,我问过台大的学生:“你们有几个人去过香港?”没有人去过。香港人倒是很喜欢旅行,可是他们旅行的时候也是购物。台湾很多人不想旅游,连留学都不想。倒是大陆有这个好处,大家都喜欢旅行、留学、游学,但经验需要积累,大家可以慢慢积累。我觉得大陆有很多有才气的作家。对于中文系,我觉得像北大,不管现在程度如何,毕竟还是保持了它的那种气氛,有它的那个人文环境,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全国最好的学生都上北大,八十年代全国最好的中学生都是报考北大中文系的。文化这个东西是无形的,在某一种环境、某一种情况之下,你就会喜欢做某一种事,比如每次我到北京,都会逛书店,买一大堆书,可是我在香港就不喜欢买书。为什么?这就是北京的环境,这种环境让你能够慢慢地积累,将来很自然地就会有伟大的作家出来。我只能这么说。

本文节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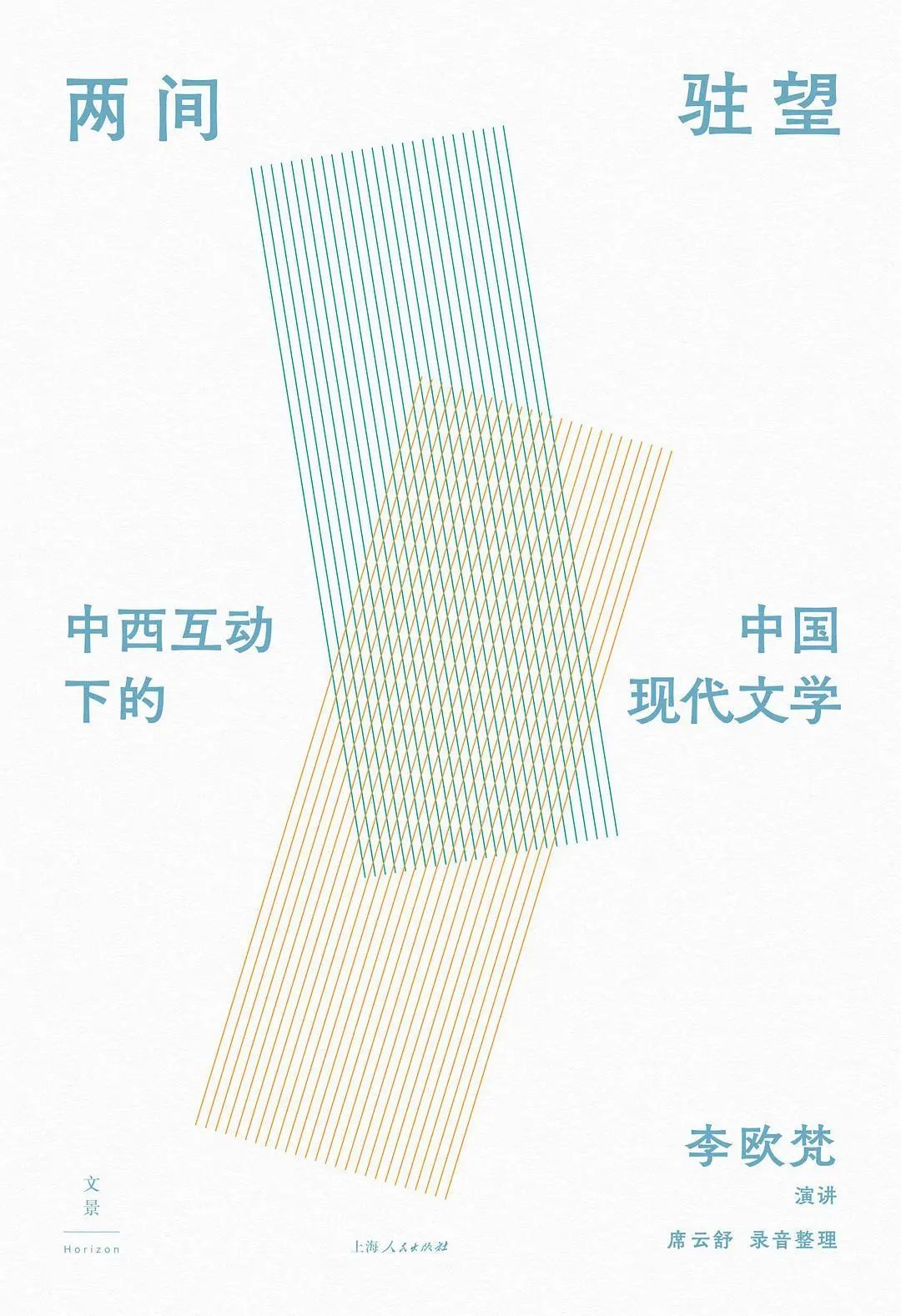
《两间驻望:中西互动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作者: 李欧梵(演讲)、席云舒(录音整理)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世纪文景
出版年: 20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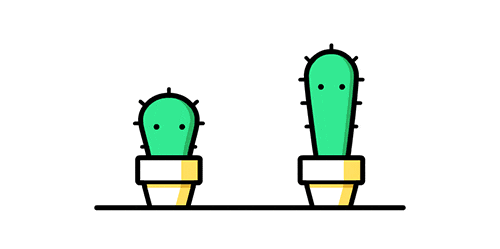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