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小说中一个小城镇医院的精神科,专门收治当地的精神病人。不过说“收治”有些过誉,因为事实上这儿只收不治,没有专业的医生,没有治疗手段,没有药物,只有一间冷落在荒芜院落的闷臭厢房,以及一位拳头粗大、头脑简单的看守人,任务是不让疯子跑出去。
小说讲述了医院院长安德烈,如何一步步把自己变成病人送进这个“第六病室”。看似荒诞离奇,实则对陈腐的社会规则、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讨论,充满了深刻的隐喻和嘲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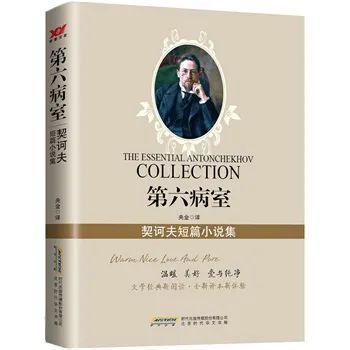
安德烈院长有修养、有理想,年轻时准备干教士行业,遭父亲强烈反对而转学医。刚来时,医院状况混乱不堪,医疗条件极差,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连温度计也没有;卫生条件极差,杂役、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满地蟑螂、臭虫、耗子,交叉传染从未绝迹;医护道德极差,从医士到院长都向病人勒索钱财,前任老院长甚至私卖医院的酒精敛财,还罗致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
面对这么个烂摊子,安德烈院长的内心是崩溃的,他认为最好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出去,让医院关门。他不断说服自己放弃这种冲动:一个人办不成这件事,况且这样办了也没用,就算把肉体的和精神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它们也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只好等它们自己消灭。他安慰自己:人们既开办了一个医院,容许它存在下去,可见他们是需要它的。也许,人世间没有一种好东西在起源时不沾一点肮脏。
安德烈院长上任后,购置了满满两柜子的外科器械,要求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房过夜……但他到底性格软弱,缺乏正面斗争和改变现状的勇气,他不能吩咐总务处长别再偷东西,也没有能力取消这个寄生的职位,看到明知是假造的账单要签字时,他的脸就涨得通红,觉着于心有愧,不过还是签了字。每逢病人向他抱怨助理护士,他就发窘惭愧,嘟哝“一定出了什么误会……”

开始时,安德烈院长工作勤奋,每天从早晨到中午一直给病人看病、动手术、甚至接生,可每天上午四十个门诊病人,掏空了安德烈院长的身体。日子一长,他彻底厌烦了这个单调无味的工作,并产生了自我怀疑:一天天、一年年这样干,城里的死亡率并没减低,病人仍旧不断地来。虚伪的医治对病人真有帮助吗?还不如将医院建得干净通风,聘请有良知的医生,重建医院的运转制度。
然而这些沉疴宿疾,哪里是安德烈院长一人就能改变的,对此他心有愧疚“一年接诊一万二千个门诊病人,就等于欺骗了一万二千人”。但谁能长久地生活在愧疚中呢?安德烈院长在挣扎中逐渐从勤奋转向了逃避,把自己关入书房,不再天天去医院了。他安慰自己:“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注定的结局,那又何必拦着他死呢?”“普希金临死受到极大的痛苦,可怜的海涅躺在床上瘫了好几年,我等普通人生点病有什么关系?”
安德烈院长更深刻的绝望和心灰意冷在于,他看到了社会规则的虚伪残酷、众人的麻木迂腐。从自己所在的小医院而言,医院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窃、污秽、毁谤、徇私上面,建立在草率的庸医骗术上面。从整个医学界而言,近二十五年医学的发展令他惊奇,甚至入迷,人们用人道态度对待疯子,不再往他们头上泼冷水、给他们穿紧身衣了,然而又如何呢?患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人们哪怕给疯子开舞会,演戏,可仍旧不准疯子自由行动,他们命运的实质没有改变。

在看似平静的书房中,安德烈院长孤独的灵魂没有找到答案,他也没能找到一个知己,倾吐这份困顿苦闷。迷茫的安德烈感到无力和悲观,直至遇见了伊万,他看到了光。
伊万是第六病室的一个病人,出身贵族家庭,做过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在他眼中,人们的生活无聊又烦闷,没有高尚的趣味,强暴、粗鄙、放荡、伪善。伊万发现普通老百姓尽管不杀人、放火、偷盗,但偶然在无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吗?而且受人诬陷,最后还有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可能发生吗?而法官、警察、医师等,时候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即使有心,也敷衍了事、冷酷无情。因此伊万想尽一切办法逃避人群,却被当成异类投入第六病室。
院长极偶然地来到第六诊室,二人的苦闷一拍即合,尽管伊万对身为院长的安德烈充满敌意,安德烈却再也不能忽视这位讲出他心声的病人。笔者认为二人对人生困境和生存方式的讨论和思辨,是整篇小说最精彩的部分。

二人相遇时对牢笼的讨论令人动容。
伊万:“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安德烈:“因为您有病。”
伊万:“不错,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十成百的疯子都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跟健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跟这些不幸的人必得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关在这儿?您、医士、总务处长、所有你们这医院里的混蛋,在道德方面不知比我们每个人要低下多少,那为什么关在这儿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道理在哪儿?”
安德烈:“这跟道德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要是没关起来,谁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人,这是既说不上道德,也讲不出道理来的,只不过是刚好机会凑巧罢了。”
伊万:“放我出去吧。”
安德烈:“我办不到。”
伊万:“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安德烈:“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处在您的地位,顶好是从这儿逃出去。然而可惜,这没用处。您会被人捉住。剩下来您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待在这个地方是不可避免的。”
二人对面对困境如何生存起了争执,安德烈院长认为应该随遇而安,而伊万指出院长鸵鸟哲学的虚伪。
安德烈:“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什么差别,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
伊万:“请您到希腊去宣传那种哲学吧。那边天气暖和,空中满是酸橙的香气,这儿的气候却跟这种哲学配不上……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依我看来,只有这才叫做生活。”

这番讨论以伊万对安德烈院长的一顿痛骂告终。
您把您的生活极力安排得不让任什么事来打搅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跟别的坏蛋去办。您自己找个温暖而又清静的地方坐着,攒钱,看书,为了消遣而思索各种高尚的无聊问题,总之,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对现实只有理论上的认识……在这儿,我们关在铁格子里面,长期幽禁,受尽折磨,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室跟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分别。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并且觉着自己是大圣大贤……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
这番话戳中了多少人的心病。人们一方面对丧、佛系、躺平等话语的调侃和反抗有种心知肚明的乏力,另一方面对职场PUA、内卷、鸡娃等话题代表的社会焦虑深恶痛绝又毫无办法。我们像伊万,在痛苦中辗转愤怒又无路可逃;我们也像安德烈院长,自我麻痹、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笔者读来如芒在背。
由于被伊万吸引,安德烈院长没事就往第六病室跑,逐渐被身边人看成异类,没人看得懂他和一个疯子的交谈和共鸣。身边人开始躲着他,同事劝他服用镇定药物,市政厅甚至组织委员会考察其智力水平……人们劝安德烈院长离开岗位,朋友米哈依尔也提出要陪他外出散散心。

正直的安德烈满不在乎地辞职了,并认为暂时离开这个城市,躲开那些把他看做疯子的蠢人,也未尝不可,然而一路上朋友米哈依尔的粗俗和平庸却令他忍无可忍。米哈依尔身为邮政局长,喜欢穿着军大衣招摇过市,看着兵士们见他都立正行礼;喜欢有人伺候,在女仆面前只穿着内衣也不觉得难为情……安德烈接连隐忍了几天,便声称生病不肯走出旅馆的房间。旅途即将结束之时米哈依尔打牌输了,向安德烈借钱还清赌债,二人草草回城。
安德烈失去了工作,只能搬去简陋的公寓。他努力保持心态平静,然而债务总让他感到焦躁不安。他二十多年手握权柄却不曾敛财,想到自己既没有得到养老金,也没有得到一次性的补助,不由得愤愤不平。然而他内心仍然在跟自己斗争,懊恼自己满脑子的浅薄思想。朋友米哈依尔欠债不还,也总令他如鲠在喉,吞吐不出。

令安德烈情绪失控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这位借钱不还、虚伪的朋友米哈依尔,他仍旧夸夸其谈:“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明年夏天,咱们到高加索去玩一趟,骑着马到处逛一逛——驾!驾!驾!等到我们从高加索回来……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好朋友……” 安德烈忽然就被激怒,赶走了同事和朋友,像发烧一样哆嗦,反复说了很久:“蠢材!愚人!”
等到火气平下来,莫名的道德感又让安德烈不断反省自己,觉得羞愧,自己的智慧和客气去哪儿了?正在安德烈和自己斗争的时候,人们都确信他真的开始发疯了,同事将他骗到第六病室后离开。在守门人尼基达的指点下,安德烈才明白这个圈套。
长夜难眠,“这就是现实生活”,安德烈感到害怕、绝望和屈辱,他进行了平生第一次激烈的反抗,用尽全身力气撞门,大喊“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主,难道下一个世界里真的没有地狱,这些坏蛋会得到宽恕?正义在哪儿……”然而他得到的是守门人尼基达毫不留情的殴打。安德烈痛苦地想到,这里的人,若干年来一定天天都在经受这样的痛苦。他抛弃了所有的自我麻痹和自我安慰,痛恨自己过去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麻木冰冷中。第二天傍晚,安德烈就因为中风而死了,他的哲学终于成了对自己的终极嘲讽。

这篇小说构建起令人窒息的牢笼意象,契诃夫在小说中点出:“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逃脱的牢笼里面。”第六病室是具象的小牢笼,当时的俄国是个大牢笼,沙俄政府进一步强化专制统治,整个社会黑暗、腐朽、令人窒息。
青年时期的列宁读完这篇小说后说道:“读完之后觉得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待不住,我站起来走出去。我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号病房’里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不也是如此吗?他进一步延伸解读:现代社会是一个大型的全景敞式监狱,从家庭、军队、到工厂、学校,都在模仿监狱来规训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这张隐秘的“监狱网”,谨慎地将权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契诃夫(1860-1904)是十九世纪末俄国享誉全球的短篇小说大师,和莫迫桑、欧·亨利一齐被誉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第六病室》是他创作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的作品具有了更强烈的批判性。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小说,文字犀利忧郁,思想的深刻隽永超越了时代,对生活和人物注重细节描写,尖刻而不失温情。托尔斯泰称其为“无与伦比的作家”,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契诃夫,远比我高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