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安妮·埃尔诺是谁?法国著名女作家,作品专注于描写个人人生经历,尤其是女性经历。根据其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影片为女性堕胎题材。
2、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颁给了她?再次兑现了“十年内必有一位法国作家”坊间定律,或许也是对女性主义和身份证治的回应。
3、说诺奖“不爱给村上春树这样的著名作家,而总喜欢发掘冷门作家”是否有根据?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2年10月6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授奖词是“因她勇敢而敏锐地揭露了个体记忆的起源、隔阂与集体压抑”。
而当颁奖现场有记者提问说“这次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安妮·埃尔诺,是不是想向世界传递什么信息?”时,评委会相关负责人只是说:“安妮·埃尔诺在文学上的质量和共性,适合每位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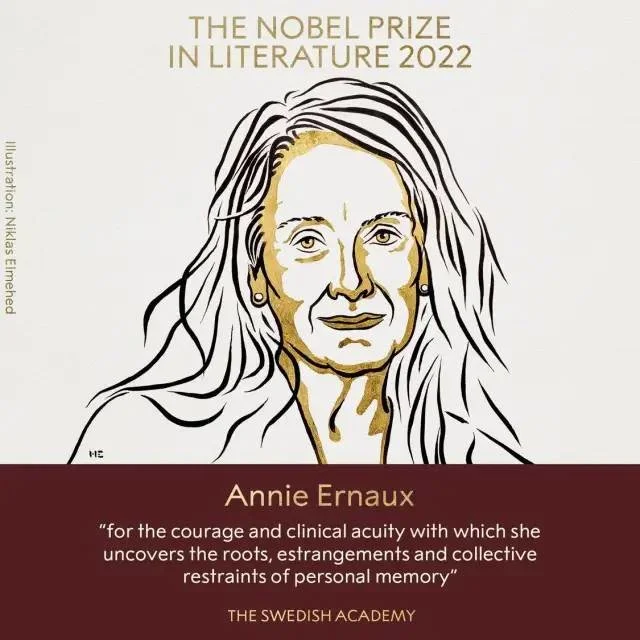
诺奖之于安妮·埃尔诺的授奖词
在世界范围内,安妮·埃尔诺的名气并没有村上春树、阿特伍德、米兰·昆德拉等作家响亮,但她的写作造诣并不低于这些作家。她为什么能够获得诺奖?下面,我们尝试大致介绍她的写作风格和主要作品,分析本届诺奖评委为什么会垂青于她。
安妮·埃尔诺是谁?
安妮·埃尔诺是一个让中国读者陌生的名字,但在当今法国,她是和莫迪亚诺、维勒贝克一样大名鼎鼎的作家,也是今年关于诺奖赔率榜的热门人选。而这一次,诺奖再次兑现了“十年内必有一位法国作家”坊间定律。
1940年,埃尔诺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在诺曼底的伊沃托小城度过了童年岁月,她的父亲是农民,后来在工厂当工人,母亲也是小手工业者,夫妻结婚后在伊沃托的一处贫困街区经营一家咖啡食品杂货店。埃尔诺从小体验了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对普通女性的生存痛感有深刻共鸣,这也是促使她在代表作《悠悠岁月》《一个女人》里反复书写女性私人史的出发点。

18岁的埃尔诺与其母亲
对埃尔诺来说,写作是一种自我救济。她在最艰难的时光靠写作打捞自己,也通过文学和写作改变了自己的生命。青年时期,埃尔诺进入法国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深造,获得教师资格证,在中学讲授现代文学课程,其后成为作家。
但在此期间,埃尔诺也曾背负父辈的不理解,后者一度认为自己的女儿背叛了她出生的世界,成为一名城市中产新贵式的文人,而埃尔诺在成长道路上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个人与社会和时代浪潮的关系,以及写作对于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受到法国新小说派、普鲁斯特、塞利纳和欧洲流行的个体化叙事的启发,埃尔诺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名叫“无人称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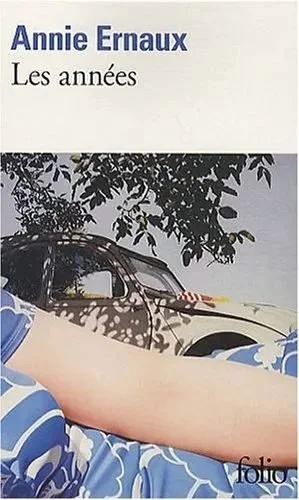
《悠悠岁月》法文版封面
在自传体小说《悠悠岁月》里,她全篇采用的叙事主语不是第一人称“我”,而是第三人称,法语中无人称的泛指代词on,近似于“我们”的意思。埃尔诺通过这种集体表述,唤醒冷战亲历者的公共记忆,也对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心灵进行了一次细腻的勘探。她以一种犹如幽灵潜游般的语调,回望了冷战时期动荡不定的岁月,在她的笔下既有政权博弈、国家冲突,也有家庭里的琐事、上班族日常的烦恼。
《纽约时报》在介绍埃尔诺时曾写道:“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埃尔诺的作品主要专注于描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她挖掘自己的记忆,并展现个人记忆与人们集体经历之间的微妙互动。不少读者认为,他们在她书里‘简单的激情’中看到了自己。”
安妮·埃尔诺写短篇的时候有一种门罗的精确性,她们共同喜欢的是契诃夫。她写长篇会人想起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塞利纳、玛格丽特·杜拉斯,还有作家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鳄鱼手记》,她们的写作都不害怕暴露自我最私人的部分,有一种向内的漩涡般的巨大能量。
她作品的可读性很高,她的书在法国就是畅销书,翻译过来,一部小说也是能一口气读完那种。流畅的意识流质感,又有很强的新浪潮电影感,跳切、横移、自我凝视、从自我延伸到社会氛围的近景、中景、远景,那种自我的对话感特别强烈。看她的小说像是看一个聪明老太太讲话,这一点其实有点像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参考《别名格蕾丝》《猫眼》两本书),又像是自己照镜子,其实是需要很大能量的写作,因为作者要不断面对自我记忆中最深渊的部分。
到如今,安妮·埃尔诺的代表作有《悠悠岁月》、《空衣橱》、《位置》、《一个女人》、《单纯的激情》、《耻辱》、《事件》、《占领》等。其中自传体小说《位置》和《一个女人》分别创造了五十万和四十五万册的销量。2019年,安妮·埃尔诺凭借《悠悠岁月》入围了国际布克奖短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安妮·埃尔诺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影片《正发生》获得了2021年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此片讲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女大学生安在意外怀孕后试图堕胎的故事,《正发生》用“少女怀孕”作为引子,揭露一个女性在社会中常遭受到的多重压力。

根据安妮·埃尔诺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影片《正发生》
其实埃尔诺的写作既可以视作女性主义写作,也可以当作一次又一次人类学视野般对于女性自我的研究,关于女性情感、身体、记忆的书写,顺应的是法国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个人书写叙事浪潮,一种打破虚构和非虚构界限的个人史。埃尔诺写作的开创性在于她不再给自己框定小说、散文、评论、非虚构文体的边界,她继承的是普鲁斯特那种“无限书写自我”、“在向内的跋涉中看见一个时代”的写作精神,但比起普鲁斯特对于贵族文人生活、男性创作者心灵史的关心,埃尔诺更重视女性的身体和情感,女性如何用自己的笔写下自我和世界,写下她们漩涡般的情感和记忆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埃尔诺也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法国女性作家。
与她同国度的埃莱娜·西苏主张:“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埃尔诺写作的开阔性在于:读者既可以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待她的创作,也可以从个体精神史、无人称叙事、非虚构与虚构混合的角度来切入。加之埃尔诺是从法国平民家庭出身的作家,所以她的创作里也不乏底层生活、市民社会的气息。

安妮·埃尔诺
安妮·埃尔诺获奖的理由
或许是对女性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回应
和去年古尔纳爆冷夺奖相比,今年埃尔诺的得奖属于一个很“安全”的选择。这个选择兼顾了文学成就、写作开创性、个人声望等多重因素。埃尔诺在法国文坛本身就是一位著名作家,加之法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诺奖上次垂青法国作家又已经是八年前的往事(当时颁给了莫迪亚诺),所以早在本届开奖之前,预测者普遍猜测今年诺奖会给一位非英语区作家,其中法语、葡语、西语概率较大。
埃尔诺获奖属于一个实至名归的结果,她的写作兼顾了文学性和畅销性,属于在新小说派里比较获得读者喜爱的一位女性作家。如果我们考虑到近几年欧美的公共议题,会发现女性主义和身份政治的重要地位,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2022年9月伊朗女性死亡事件、2022年10月初法国多位女演员在直播时剪发,以此来声援伊朗女性的抗争,都可见女性赋权、女性联结在今日欧洲已经是不可忽略的议题。
与之对照,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反乌托邦写作、乌利茨卡娅对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女性命运的描绘等等,都可见女性写作在今日文学世界的力量和厚度,女性写作不只是一种口号,它成为了一种解放性的力量,从安妮·埃尔诺、埃莱娜·西苏到费兰特、阿特伍德,她们为我们展现了广袤的女性文学世界。

24岁时安妮与丈夫的合影,当时他们住在波尔多。安妮刚刚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儿子。
另一个层面,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会发现评委对于离散叙事、身份政治、个体主义写作、意识形态撕裂与国家冲突所导致的存在主义困境有一种持续的关注。
比如2021年诺奖授予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的颁奖词是:“因为他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 2017年诺奖颁给石黑一雄的时候,颁奖词也提到了全球化下新的危机:“他的小说富有激情的力量,在我们与世界连为一体的幻觉下,他展现了一道深渊。”
对于个体和写作形式的关注也体现在对露易丝·格丽克的评语:“因为她那毋庸置疑的诗意声音具备朴素的美,让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具有普遍性。”在颁给托卡尔丘克那一年,授奖词有一段:“她赋予原本无名的女人以个体身份,赋予原本消失无踪的仆人以发声的权利。”

安妮·埃尔诺与自己的两个儿子
记录时代洪流下的个体命运,成为诺奖评委的审美偏好。安妮·埃尔诺的写作恰好符合这一点。她探索的是一种用人类学方法观测自我的写作,在浓度极为强烈的个体暴露中,呈现出历史给个人留下的伤口。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春天,埃尔诺曾经到访中国,先到北京,后到上海,应邀出席文学活动。她在对于中国的回忆中写道:
“我在街道和建筑工地的喧闹中、在偏僻的胡同和公园的宁静中漫步。我在最新式的高楼旁边呼吸着平房的气息。我注视着一群群小学生,被货物遮住的骑车人,穿着西式婚纱拍照的新娘。我怀着一种亲近的感觉想到‘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不一样,但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我看到的一切,在卡车后部颠簸的工人,一些在公园里散步的、往往由祖父母、父母亲和一个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和我当时正在撰写的长篇小说《悠悠岁月》产生了共鸣。
在中法两国人民的特性、历史等一切差别之外,我似乎发觉了某种共同的东西。在街道上偶然与一些男人和女人交错而过的时候,我也常常自问:他们的生活历程是什么样的?他们对童年、对以前的各个时期有着什么样的记忆?我会喜欢接触中国的记忆,不是在一切历史学家著作里的记忆,而是真实的和不确定的、既是每个人唯一的又是与所有人分享的记忆,是他(她)经历过的时代的痕迹。”
诺奖为什么不颁给村上等更出名的作家?
颁给更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人
诺奖无潜在规律可言,妄图给它整理出一套评选规律,无异于自讨苦吃。改革评委会后的诺奖,只有几个潜在共识:一、男女作家比例更平衡;二、走出欧洲中心主义;三、在写作上具有创造力,而不只是前人风格的简单模仿。2018、2019年给了托卡尔丘克和彼得·汉德克、2020年露易丝·格丽克、2021年古尔纳,性别平衡、语言和地区平衡,都有体现。
唯一有争议的是这些作家大多处在欧洲,坦桑尼亚出身的古尔纳,其实也在英国定居,用英语混合桑给巴尔语的方式写作。但也可以理解,欧洲仍是目前最强势的文学土壤,英语写作也是世界上最主流的写作方式,诺奖评审们身处欧洲,参考奖项又是布克奖、布克国际文学奖、卡夫卡奖等,在欧洲生活的作家更容易被看见,乃是客观现实。
诺奖评选有个潜在传统,叫做“给小不给大”。简单来说,尽量不给已经当世德高望重、经典化、不需要诺奖傍身的作家。比如“英国移民文学三杰”,诺奖给了奈保尔、石黑一雄,2021年给了研究拉什迪的古尔纳,愣是不给三人名气最大的拉什迪。无他,或许拉什迪已经不需要诺奖证明自己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过很多如雷贯耳的作家,都没得诺奖。比如:博尔赫斯、卡夫卡、普鲁斯特等。
所以,像T·S·艾略特这样已成诗界经典,又获诺奖的,在诺奖历史上,并不是一个高概率事件。诺奖评委更喜欢写作技艺精湛、有潜力经典化、但还没有获得世界声望的作家,比如托卡尔丘克、石黑一雄、露易丝·格丽克,颁奖之前,他们在各自的文学圈子都挺被认可,但还没有被世界读者熟知。
一言以蔽之:诺奖评委喜欢抬人,不喜欢后知后觉。
他们不会没听过那些大作家的名字,比如阿特伍德、维勒贝克、米兰·昆德拉等,甚至可能他们私底下也很喜欢,但让他们评奖,他们也会有自己的算盘。比方说:给这个人意义大不大?Ta还需要诺奖吗?Ta虽然名气很大,可真的有那么好吗?
当然,诺奖也非常在意“不可替代性”,有些知名作家的确名声很大,但有一定的可替代性,作为一个可能代表全球最高水准的文学奖,不可复制,是应该具备的基本考量标准。
作为中文读者,比起把诺奖颁给作品已经蜚声世界、不缺乏多国译本的作家,我们也乐于见到诺奖颁给一位风格具有创造力、水准惊人,但仍然缺乏中译本的作家。
很喜欢诺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一句话:“写作是一种拉伸运动,它拉伸着我们的经验,超越它们,建立起一个更广阔的意识。”
无论诺奖争议如何,但至少,在一个文学声浪式微的年代,每年有这样一个时机,让我们重新讨论文学,哪怕是出于一时的好奇心,看到世界上另一个角落的作家,他们的广阔意识和写作实践,至少在那一刻,文学仍然能给人出神的体验。那是一个我们走出麻木的时刻。好的文学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出神与惊醒。
| 